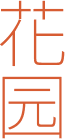作品:曾骑铁马入重城
一、大铁壶
早春时节,东风吹着汴河的水,发出哗哗的声音,白浪层层,宛如镜上浮花。两岸隋堤,柳条儿方抽了新芽,在蒙蒙的晓雾中初绽一年的烟绿。
河上舟船如织,东水门外更见一艘收了白帆的巨大货船,满载着东南方物,缘北岸逆波而上。
那船上牵出八根纤绳,连至北岸之上,有十几个精壮纤夫,正绷足了一身的力气,要将船拖进码头卸货。
纤夫之中,一个较众人矮去半头的汉子格外显眼。他身不足七尺,皮肤黝黑,塌鼻梁厚嘴唇,颔下生着些短须,看去约摸三十外岁,一头黄发不梳不绾,却以碎布随意一捆,高高束在头顶,一望便知不是本地人氏。
早春天气尚寒,那汉子已光了膀子,仅着一件单衣,却把上衣扎在腰际。纤绳虽也细细裹了布,但仍深深勒进肩头。
汴河码头上的纤夫是包工,做多做少都是一天三顿饭、三十钱。众人都是老做工的,晓得怎么偷懒,拉纤不过高高儿使上七八分的劲头。这汉子却不拘力气似的,愣支着身子骨跟纤绳较劲,仿佛一个人就要把整艘船拉动。
他周身的筋肉都鼓突着,像是随时要把那些粗布绽碎。朝阳照在他倾斜下去的背脊上,忽然被什么银亮亮的东西反射了,汇聚成一个灿烂的光点。
那物件乃是个一掌见方的大铁壶,就挂在那汉子的裤带上。壶形状粗陋,不见什么花纹,只是面儿上磨得光光的,壶身宽大,壶嘴儿却细细直直,足有两寸多长,顶上塞着麻布片儿裹的壶塞。
这壶跟他的主人一样,不仅不大好看,还透着些怪异。那绯服乌纱的公子打马而过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奇特的大铁壶。
他路过的时候,正逢纤夫们拉完了一次活儿,扎堆坐在码头上休息。那黝黑的异乡汉子叉开两腿,坐在一个石礅上,拔了壶塞往嘴里倒着什么。
几个纤夫围上来,其中一人道:“南边儿来的,给我也喝一口。”
汉子放下铁壶道:“是酒,不是水。”他操着浓烈的越地口音,不仔细分辨,东京地方的人很难听懂。
纤夫们听见他古怪的口音都哄笑了起来。有人翘起大拇指道:“大清早便喝酒,你行。”
之前那人也笑嚷道:“是酒更好哇,爷的酒虫许久没祭了。快快!给我喝一口!”
那汉子面无表情,默默递了壶给他。那人用袖口擦了擦壶嘴,仰脖儿咕咚灌下一口,立刻就喷了出来,淋淋洒洒弄得一身都是。他不住咳嗽道:“南蛮子,你这酒坏了,恁般难喝!”说罢把铁壶狠狠一摔。
那汉子大手一抄,稳稳接住,仍旧是面无表情,也不再说话,自个儿又闷闷地喝了几口。
纤夫们见他冷冰冰的不好相处,也不去招他,一齐嘻嘻哈哈地走开了。那汉子独自坐着,除了喝酒,便只是低头瞧着自己孤零零的影子。
忽然,那影子上叠过一个巨大的马影来。他猛抬头,就看见一名绯服乌纱官人打扮的青年公子,牵着一匹鞍辔华美的枣红马儿,笑吟吟站在他面前,道:“这位大哥,你那壶中的好酒,可愿舍我一杯尝尝么?”
汉子定定瞪着那公子。
汉子有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眼窝深陷,眼白布满了血丝。可他眼里丝毫不见苦人儿的疲态,却有一种再多愁苦也掩不住的精光,毫无顾忌地迸射而出,落在眼前人的身上。
汉子瞪了那公子一会儿,又不声不响地伸直了手臂,把大铁壶递了出去。
那公子又笑一笑,接过壶,擦也不擦便饮。他却没料到那壶中酒竟是出乎寻常的呛辣,一口下去,喉管里浑如着了火,强往下咽时,那火就一顺儿烧灼下去,毫不留情。
不过一刹,那公子也“噗”的一声把一口酒喷了出来,污了官服的前襟。他辣得眼泪都要流出来,连声道:“厉害厉害!”
汉子站起身,轻轻把铁壶拿回,自喝了一大口,脸上并无痛苦之色。这极烈的酒在他喝来,就好像清水一样。
他咽下那口酒,晃一晃铁壶,冲那公子开口道:“还要不要?”
那公子大笑道:“要!”
他抢过铁壶,又饮下一口,这一回硬是咽了下去,只是饮毕就忙张嘴哈了口气。
那汉子依旧拿回壶来,自喝一口,冷冷又问道:“还要不要?”
那公子哈着气,道声:“够劲!”接过壶又喝了一大口。
汉子拿回铁壶,将残酒一饮而尽,又将壶塞塞好。壶中酒炽烈非常,连这豪饮的汉子双颊也被熏出了一片殷红,本就满是血丝的眼睛烧得更红,像是随时要滴出血来。
河上又有大船靠岸,纤夫们聚了赶去接活儿。包工头儿骂骂咧咧地呼唤那汉子:“混账蛮子!偷的什么懒,大清早的死灌黄汤!还不滚过来上工,爷这里可不养闲人!”
汉子猛冲冲站起,神情已带了七分酒意。他把大铁壶顺手挂回裤带上,看也不看那公子,兀自转身,一步一晃地向同伴们走去。
他走了几十步,扶着一株大柳树站住。
和风吹着前朝故柳,柳丝拂在汉子滚烫的脸上、通红的眼上。他呼出两口浊气,将身站得笔直,突然高声唱起一支歌来,复又大步向前。
那歌声高亢婉转,乍听去竟有些悲怆之感,仿若一只无形大手,在人的心上遽然一握。
那公子牵马立在原地,遥遥听着。他只听得懂第一句,似乎是越人俚歌中常有的开头:
“今夕何夕兮——”
而其后种种,却再不能一一辨明。
那汉子旁若无人地高歌前行,直至他重又背上纤绳,那歌声才戛然而止。
那公子引着马儿转了头,踱到工头儿的面前。那包工头儿认出他穿的是皇家四品武官服色,慌忙屈膝跪了下去:“小的见过郎官大人!”
公子道:“起来吧,我有点子事要问你。”
工头儿低头哈腰,畏畏缩缩站着,小心翼翼道:“郎官大人尽管问。”
公子遥指着那汉子道:“那位带大铁壶的南人,唤做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工头儿道:“他来了才五六日,只登了名字叫做什么‘长慧’,连个姓儿都不会写……他都是自个儿走来上工,力气是好的,却也不与旁人啰嗦。他家住在哪里,小的真的不知……”
公子点头道:“今日收工时,你代我问一问他。明日我再来问你。他若问时,你就说是一个姓展行三的打听,想与他交个朋友。”
工头儿诺诺应了。那公子也不多言,一捋缰绳翻上马背,迎着艳阳下东京城青灰色的城墙,翩然而去。
二、木屐女
展三公子第二日再去码头时,带着大铁壶的长慧已没了踪影。包工头儿吓得半死,生怕这位郎官大老爷怪罪,跪地一个劲儿地求饶。
原来那名叫长慧的南人听了工头儿代问的话,当即转身,走了几步便不见人了,竟连当日的工钱也顾不得支。工头儿赌咒发誓,认定这个长慧是南边来的逃犯,不然怎么这般惧官,连高攀的机会也错过。
展三公子却只叹了口气,掏出一锭银子赏了工头儿,便自去了。
打从那日起,三个多月不觉过去,他真个就再没见过长慧。
时光如流水,惯看花开花落,任凭春来春去。隋堤上的柳色从无到有,再到葱葱茏茏,白絮翻飞。
转眼已是六月初六,崔府君的生辰。这算得汴梁每年的一大盛事,万胜门外戏棚、围场交错,排开南北新剧,演绎缘竿、拔距,端是百戏纷呈,乐声杂起,观者如潮。
这日京中无论贫富贵贱,人皆外出游玩。街巷内孩童嬉闹,欢乐非常。新曹门外贫人聚居的牛行街末瓦片里虽无戏摊光顾,也有一群十来岁的半大少年用木叉竿支了球门蹴鞠玩耍。
一众少年当中,独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穿一件用男人衣服改制的破短衫,一条旧长裤,没有着裙,绾了两个鬏儿,满脸都是污垢炭灰。女孩连鞋子都没有,光脚靸着双大木屐,笑嘻嘻混在男孩堆里跟着去争那鞠球。
她虽穿着厚重木屐,闪身却分外灵活,就连穿着薄底布鞋的年长少年也拦她不住,几个来回追逐下来,那球就到了女孩的脚下。
女孩重重一脚撩在球上,鞠球挟着力道疾旋而出,径自从大街的这头飞到了那头。街对面正走着一位穿着考究青衫的公子。那人似是听见风声,恰恰转过脸儿来,眼瞅着那球就奔他的脸上去了。
少年们都惊叫起来,以为这一下必要砸到那贵公子的脸。那女孩也急得张大了口,却没发出什么声音来。
不料那青衫公子不慌不忙,待那鞠球近了,轻轻向上一纵,肩头巧妙一带,便卸去了球上的旋劲。他足未落地,身子已在空中一拧,那球滴溜溜地从他的肩头落到胸口,颠上一颠,又弹了起来。他又突然一个大翻身,横腿猛扫,将那球一瞬间又扫过了大街,重重砸在简陋的球门上,把叉竿儿也砸折了一根。
少年们先是怔愣,忽然齐刷刷拍着手儿叫起好来。唯那女孩只是拍手不见出声。
那青衫公子挠着头踱过大街,花花的日头照见他年轻端正的脸,他正是三个多月前打马隋堤的展三公子。
展三公子挠着头,问道:“刚才那一球谁踢的?”
少年们急忙散开,十几双脏兮兮的小手一齐指着那女孩:“她!”
那女孩也不逃跑,站在原地默默点了点头,好像也承认了闯祸的是自己。
展三公子弯下腰去,双手按着膝,把脸儿降得和穿木屐的女孩一般高,笑道:“小妹妹好脚力,差点把我的头也砸歪了去!”
那女孩咬着嘴唇,瞪大眼睛直直地望着他。
展三公子又笑道:“敢跟我比比么?若你赢得了我,我送你一双鞋。”
那女孩转了转黑黢黢的眼珠儿,然后微笑起来,点了点头。
少年们立刻忘记了害怕,再度欢呼拍掌起来,有人嚷道:“秋囡,同他赛井轮!”
这“井轮”之赛,是要以头、肩、胸、腹、膝、足接触鞠球,做出飞异、滚异等种种花巧,一赛控球的长短,一赛运球的技巧。
那唤做“秋囡”的女孩又点了点头,晃两脚踢飞了木屐,光着足尖挑过鞠球,背转身倒蹶了脚一踢,那球“砰”的一声直飞起两丈来高。
秋囡不等球坠下来,就已双脚使力蹦了上去,用头将球又顶上丈余。她先落了地,瞧着那球将将落下,急忙将身向后一俯,用胸腹去接。她娇小的身子几乎折成了一个直角,光着的脚板踏在满是碎石尘土的地上,却能稳稳站立。
展三公子却在此时一舒手臂,将那球抢先接了,托在手里。
他哈哈大笑了两声,道:“得了,我像你这般年纪时,可没这样的好功夫。我认输了,走,跟我买鞋子去。”
秋囡挺直了身子,愣愣地把他上上下下看了又看,仍旧不说话。
少年们听他认输,欢呼更甚。那展三公子指着之前折断的叉竿道:“这叉竿又是谁家的,也该我赔。”
话音既落,自有出叉竿的少年嬉皮笑脸伸手问他讨钱,少不得暗地里抬高了歪价。展三公子也不还价,照数给赔了。
展三公子赔过叉竿,还了鞠球,这才转脸问秋囡道:“你是叫做秋囡么?你多大了?”
一旁的少年嚷道:“公子爷不用问了,她跟乌龟河鱼一样,是个哑巴!”
这回轮到展三公子微怔了。他又挠了挠头,也不再问什么,便向女孩伸出了手:“秋囡,跟我买鞋子去。这是我输了给你的。”
那小秋囡却不肯握他的手,只是低头寻过自己的木屐又穿上了,掉脸朝着炊烟袅袅的里弄深处奔去。
展三公子不禁一怔,跟着往里追了几步。此地的茅屋草庐一间挨着一间,道路错综复杂,那女孩极为灵活,拐了几拐就把他甩脱了。他穿着华贵的衣服,站在整个皇城一带最潦倒的屋舍间茫然四顾,显得格格不入。有贫人见到他这身打扮,就急忙避了,一时间连个可问之人也找不到。
他又拐过几间屋,遍寻不着,只得悻悻然转身。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一个带着浓重南方口音的童声在自己身后唤道:“阿叔!”
展三公子应声回眸,看见方才那名叫秋囡的哑女,一手牵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一手抱着个旧木桶。
那小男孩仰头望着展三公子道:“阿叔阿叔,我阿姊说你是好人,她要请你吃饼。”他的口音虽然稚嫩,却与三个月前带着大铁壶的越人汉子长慧十分相似。
展三公子瞧见木桶子上果然搁着一摞薄麻饼,他的唇角顿时弯起一道弧线,眯着眼睛笑了起来:“好啊!”
这一大两小也不挑地方,就挨着墙根席地而坐。展三公子脱了青绸长衫,顺手一卷搁在地上,挽起袖子接过那木桶,掀起薄饼一看,桶里原来盛着小半桶拿油盐粗粗焯过的豆生。
秋囡用麻饼卷了一把豆生,双手捧给展三公子。她的双手和脸孔显是已经仔细洗过,虽算不得白嫩,却也是干干净净模样。
她黑黑的眼睛像是要溢出两汪秋水来,那眼睛里明明白白地映着挽着袖子的展三公子。这也许是她一生中第一个存了念头要主动结识的人,然而她却着实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待客。
展三公子接过麻饼便咬下一口,一边大嚼一边大赞道:“好吃!”
哑女秋囡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麻利地又卷好一张饼,这回是递给了一旁的小男孩。
展三公子一边吃饼,一边指着小男孩问秋囡道:“他是你弟弟?”
秋囡微笑着点了点头。那小男孩咬着饼含混嚷道:“我叫海儿!”
展三公子道:“本来是我输给你,却变成你请我。嘿,你莫笑我脸皮老,这饼真不错,麻烦你再帮我包一张吧。”
秋囡微笑着点头,正要动手,突然半空中炸炸响过一声,把她惊得一颤。
那声音怒斥道:“秋囡!海儿!还不回家去!”
那赫然是长慧的声音!
展三公子闻声抬头,就见越人长慧穿着破单衣,大敞着怀,满面满颈的污汗。他就站在五丈开外的屋舍边,脸上愤怒莫名,好像随时都要冲过来,一口咬在展三公子的身上。
他的裤带上,依旧挂着那个磨得光光的大铁壶。
三、老骡车
长慧怒冲冲过来,一巴掌打在秋囡的头上,又伸手抱起海儿,扯了秋囡就要走。
展三公子忙跳了起来,抱拳道:“长慧大哥,真是山水有相逢!你可记得咱们见过?在下姓展行三……”
越人长慧冷冷扫过他一眼,放下孩子,突然咕咚跪倒在他面前,重重地给他磕了一个响头,大声道:“展大老爷,孩子不懂事,开罪您的地方还请老爷多多包涵!”
展三公子被他这个头磕得脸色也变了,口中道:“长慧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伸手去搀时,长慧已经自己站了起来,牵着一双儿女掉头就跑,活像躲避瘟神一般。
展三公子瞧他这副模样,明白纵使追去也是自讨没趣。他退回街边,寻了方才一起蹴鞠的少年们问明了长慧家的方位,自个儿悄悄地绕了过去。
原来长慧家住在里弄深处一座独草屋,屋外以木板隔了矮墙小院。展三公子找过去时,屋里正传来女人和孩子的哭声,还有什么东西抽打在皮肉上的声音,却听不见什么人呼痛。
展三公子蹲在矮墙下听见,猜到长慧必是生气秋囡搭理自己,痛加责打,心中自然紧得发疼,眉头也不觉拧在了一处。
他实是想进去相劝的,又担心长慧见了自己打得更凶。他能劝得一时,总不能将那女孩带走。
他正急得不住,用手扒着木板缝儿朝院子里瞅,就看见海儿哭得满脸眼泪鼻涕,从屋里跑了出来,扑在木板壁上。
他不偏不倚,恰恰扑在展三公子偷看的那条缝上,小圆眼睛瞅见外面的人,眼泪还没干,就又挂上了笑。他张大了小嘴,一声“阿叔”就要喷出口来。
展三公子隔着板壁急忙伸手指放在嘴边轻轻“嘘”了两声,海儿灵巧得很,立刻牢牢闭上了嘴巴。
这时一个干瘦的女人披头散发地追出来,一把抱起他又回了屋里。
那天晚上展三公子在朱雀门外州桥夜市上买了一双合色布鞋,又转回瓦片里。他来到长慧家的小院外时,院子里的独草屋早就熄了灯火。
他站在暗地里想了想,将那双布鞋在泥面上蹭了一蹭,又用力揉过,方才隔着矮墙,把一只鞋丢了进去,砸在草屋的门上。
长慧果然警醒得很,立时便应声道:“秋囡,出去看看。”
秋囡点了一根蜡烛头儿,披着衣衫光着脚推门出来。烛光映见她的脸上臂上,一条一条分明都是青紫的伤痕。
她先是看了看左右,一低头便瞧见地上的鞋,微微肿起的小脸上顿时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展三公子不声不响,把另一只鞋儿轻轻丢了进去。他看见那女孩赤脚站在泥地上,双手捧起鞋子,仔细吹着上面的泥尘。
直到这一刻,他方才慢慢解开拧了一整天的眉头。
小屋的门吱呀一响,长慧也走了出来。
秋囡吓得慌失失想把鞋子往身后藏。她父亲早已瞧见,伸手夺了过去,凑着烛光看了看,低声道:“既是别人不要的,你就留着吧。”
说罢他把鞋子塞回女儿的手中,一转身回屋去了。
这算是展三公子平生第三次见着长慧。他再碰见这人,又已是两个月后,八月秋初。
八月秋初正是多雨的时节,天街之外道路大多泥泞,沿河两岸处处忙着固堤修桥。
这时节,悠闲富庶的人们一望见窗外连绵的雨,一想见满地坑坑洼洼的水,都不免打消了出门的念头。许多吟荷咏柳、伤春悲秋的婉词妙句,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对着自家精巧的阆苑小池,一字一字地拈来。
汴河上的商船却不得闲,就算在这时候,也是往来交通,川流不息。
关老汉也不得闲。就算在这时候,他也天天儿驾着他的老骡车,往码头上去拉货挣钱。
关老汉今年五十挂零,是老东京人,打小就住在这儿,几代人都靠在码头上接货送货为生。这天他接了一百匹上等锦缎,分作两拨,用骡车拉进城里去。
天才下过雨,刚筑高的河堤面上大坑连着小坑,泥沙混着雨水,早和成了浓浆。关老汉瞅着天色不好,生怕又赶上大雨,湿了锦缎,急得使鞭子猛抽他那两头大青骡。
偏有头骡子突然闹起了脾气,将蹄子一住,再不肯走;另一头却不省得,还在拼命往前拉。那沉重的车架子一时稳不住,顿时就歪进了泥泞之中。车上遮挡的旧布滑落,露出上等锦缎柔和的丝光。
关老汉年纪大了,哪里抬得动几百斤的车架。他忙向周遭呼救,一时也没个帮手的上前,看热闹的倒来了不少。
一群常在码头寻衅的泼皮少年凑过来瞅见,不知是谁嚷了一声:“取货啊!”突然齐冲上前,各人抱了一匹锦缎便跑。
他们一个个吃了兔子似的,撒丫子散得贼快,关老汉哪里拦得住,直急得老泪纵横。他扑在泥泞中,捞住跑在最后面一个泼皮的腿脚,紧紧抱着,连声哀告道:“大爷高抬贵手,这货实在不是小老儿的,小老儿可赔偿不起哇!”
那泼皮挣不脱,又见围观的人群中有人直嚷着要去报官,心里发急,一边骂道:“老狗才,恁地缠人!”一边抄起怀里的锦缎,就向关老汉的头颅砸去。
那锦缎挥到半空,却没能落下——一只粗壮的大手恰赶在这当口从人群中伸出来,一把将那泼皮的胳膊托住。
手的主人是个黝黑矮壮的南人汉子,精赤着上身,裤带上挂着个磨得光光的大铁壶。
关老汉认得这汉子是南边来的越人长慧,忙道:“长慧哥儿,搭救我则个!”
那泼皮想从长慧的手里拔回胳膊,可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也拔不得。长慧的五根手指就像是铁爪一样嵌在他的胳膊上,他痛得叫唤起来:“爷爷……且饶我这次……”
长慧并不答言,又伸一只手把那匹锦缎夺下,放回车架上,这才松开了手。
那泼皮得了便,猛一脚踹开关老汉,抖开一个拳架,嚷道:“方才你是偷袭,忒欺负人了!爷爷我也曾习过枪棒开过褂子行,如今公平合理,你可敢再与爷比划比划么?”
长慧默默望着他,像一尊雕像般杵在那里,动也不动。
那泼皮自以为他输了阵仗,得意洋洋招着手儿道:“不要说爷爷欺负你这南蛮子,你来呀!来呀!爷爷先让过你三招……”
他话音还未落,便觉一件重重的物什砸在自己的背上,眼前一黑,登时没了知觉。
围观众人却看得清楚,砸着那泼皮的可不是什么物件,而是另一个趁乱抢了锦缎逃走的少年。
那少年从天而降一般跌了进来,不偏不倚砸倒了同伴,且兀自仰面朝天歪着嘴巴口吐白沫,显然也神智不清的。
人圈儿外面响过一句朗朗的话语,一位年轻武官骑在枣红骏马上,执鞭抱拳,冲那南人汉子招呼道:“长慧大哥少见,可还记得我么?”
这武官身着墨黑的禁军软便袍,头戴乌纱,腰下挎了宝剑,更显气宇轩昂。他分明就是展三公子。
人们纷纷回头瞧他,关老汉人头最熟,早认出他的身份,忙分开众人上前作揖:“展大人!您来便好了,就是这几个小破落户抢了我的货!”
众人有觉得这位郎官眼熟的,听见关老汉唤出他的姓氏,也一个个转过弯来,忙七嘴八舌地指点抢夺锦缎之人逃去的方向。
展三公子翻身下马,拱了拱手道:“各位父老少安毋躁,方才本官奉命巡堤,见这贼囚跑得慌张,便顺手将其拿下。人赃并获,他已自招认了,余众本官亦已着公人缉拿。现下还请各位父老先让一让,我先帮老哥哥把车子起出来,免得拦了道路。”
众人欢呼一声散了开去。自有人帮忙牵马,也有人绑了两个泼皮押到一边,关老汉则解下两头骡子拉开了。唯有长慧还站在原地。
展三公子挽着袖子,笑眯眯道:“长慧大哥可是要帮我抬车子?”
长慧皱了皱宽宽的眉头,没有接他的话,只是即刻转身,一双草鞋已踏在泥里,两手扶住了车架的一端。
展三公子把官袍下摆掖在腰里,双脚也踩进那泥坑,伸手扶住了另一端。
两人一起发力,当时就把一整副车架连车带货都托得悬了空。他俩又协力向前行过二十来步,才将车子安放在平整之处。
路上百姓瞧见,一个个都喝起彩来。
展三公子的裤腿快靴早糊满了泥,他抹了把额汗,转脸儿冲着长慧一笑:“可热死我了!长慧大哥,你那壶里还有酒么?我想喝一口。”
长慧仍是冷冰冰的,他摇了摇头,绕开众人便走。
展三公子也不生气,顺手拉过喜孜孜的关老汉低声道:“老哥哥我问你,可晓得这位长慧大哥如今在哪里做活?”
关老汉道:“回展大人的话,他如今是在西河挖河筑堤的。别看人穷得叮儿当,却真真是一条好汉哩。”
四、长铗客
入夜,又是好一场大雨。
大雨中,一个头戴斗笠身穿蓑衣的男人踏碎了一地水花,步入了瓦片里的深处。
这人径直走到越人长慧家的小院外,站在雨中,呆望着独草屋内昏黄的灯火。
长慧开了门,倾出一瓦盆的水,抬头间便看见那戴斗笠的人。
那人也看见了长慧,他推开小院的板门,取下头上的斗笠,露出一张英俊不凡的脸来。
这样的一张脸,本是不该出现在此情此景、如此这般的一个地方的……然而这张脸的主人,更突然屈了双膝,面向穷苦的长慧,跪倒在一地的雨水泥泞当中。
那人的脸上已经分不出是雨是泪。
那人在大雨里跪地哭喊道:“大哥!”
展三公子冒雨踱到长慧家附近的时候,看见的恰巧就是这一幕。他本来撑着一把伞,此刻只得收了伞隐在暗处,任凭风吹雨打。
长慧赤着脚站在屋门边,点了点头道:“你回来了,很好。雨大,进屋吧。”
那人走到门前脱了蓑衣,展三公子看见他的背上居然背着一柄装饰华丽的长剑。
挖河筑堤的苦力工,带剑独行的江湖客,两种人看来天差地别,却偏偏在这样一个潇潇雨夜,相会在皇城根儿一个简陋的草屋中。
展三公子叹了口气,伸手挠了挠自己的头,这才发现头发已经湿得打了缕。
他着实好奇,干脆弃了手中的伞,翻过矮墙贴身在草屋外。
屋内传来长慧独特的声音,道:“当日我赶到你家,只来得及救护你的娃儿,你的妻子父母都已遭了难。这些事,你想必都已知晓了。”
长铗客的声音哽咽道:“因我逞这一时之气,连累全家老小的性命!我……我可还算是个人么!”
长慧道:“你为他人出头,本意是好的,只是你的仇家太恶。我知会你逃出关外去,本以为一人做事一人当,谁知道他们连你的家人也不放过……唉。”
长铗客道:“大哥,我在关外练剑五年,就是为了今日回来报仇!”
长慧叹道:“已经过了五年,人事全非,你的仇家死的死亡的亡,你这仇又要找谁去报?如今你可把海儿领回去,好好教养成人,也就不枉他从灭门的惨祸中捡回这条小命了。”
展三公子听到这里,不禁大愣——原来那小男孩海儿,竟不是长慧的亲身骨肉。而这越人长慧既能从灭门惨祸中救出一个婴儿,并为逃亡关外的兄弟抚养孤儿五年之久,显然也绝非泛泛之辈。
这样一个人,明明也该是挟刀带剑冠盖打马的豪杰,却怎的甘愿拖家带口埋没在市井穷巷内,做那挖河筑堤的苦力?
长铗客静了片刻,又道:“大哥说的是,我的仇就此罢了……但大哥你的仇呢?大哥的仇,我愿代你去报!”
他这话说得十分激越,长慧的反应却是平平。长慧低声道:“我没有仇,我只是受人恩惠,便要报恩。”
长铗客道:“报恩也罢,报仇也罢,横竖就是杀了那人罢了!大哥为此人困在这里多时,我来替大哥办了这事吧!”
长慧厉声喝道:“混帐!你以为杀人只是一剑之事么?”
他这声炸雷一样,轰破了绵绵的雨幕。不仅那长铗客应声沉默,连屋外的展三公子听了,也仿佛被施了定身咒儿,垂着双手沉在原地。雨水已将他的一身透湿,他却浑然不觉。
往后他便再没听到任何言语。或许是屋内的人相顾无言,又或许是他们的声音小了下去,很小很小,以致终于被淋漓喧嚣的雨声湮没。
约摸一炷香过后,长铗客重又开门走了出来,披回蓑衣斗笠。
他仍旧是孤身一人。
长慧手里端着一盏旧油灯,送他到门口,道:“你真的不带海儿走?”
长铗客道:“有大哥教养,他必不会像我这般四处闯祸。”
长慧叹了一声,道:“若我死了呢?”
长铗客道:“大哥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长慧道:“不必,我断不会死。你的儿子既然放心给我,我定会好好教养他成人。”
长铗客听到这句,也自长叹了一声,与长慧一拜而别,转眼消失在深黑的雨夜里。
长慧并不退回去,只待他去得远了,才向展三公子栖身的方向晃了晃灯火,冷冷道:“你淋了多久了?要进屋么?”
展三公子拖着一身水湿狼狈地走了出来,却抱拳笑道:“长慧大哥少见,屋里可有姜汤么?”
长慧上下照了照他,忽然一牵嘴角,露出一个笑容,低声道:“有。悄悄儿进来,别吵醒娃儿们。”
这竟是展三公子第一次看见他笑。
展三公子蹚着水走到门前,把靴袜都脱了,也赤着脚走进去。长慧引他来到屋内,把油灯放在屋子中央唯一的破木桌上。
那木桌只得三条腿儿,第四条腿垫着一摞砖,瞧去便有点歪。桌上摆着个大瓦盆,正接着屋顶上漏下的雨水。屋子一角是灶,另一角便是炕。
炕上只一条打满补丁的大被,被下蜷缩着一大两小三团人形,都紧紧倚靠在一起。
长慧捡了两块柴丢进炉灶,一边扇旺了炉火给展三公子热着姜汤,一边指了指炕上的三个人道:“我的婆娘、阿女、小子,你是不是都见过的?”
展三公子点了点头,脱下湿透的外衣扔在门边地上,蹲到灶边专心烤火。
长慧让了让,转脸望着他,眉头紧皱。
那一夜,直到展三公子饮罢姜汤离去,这越人汉子都没有再吐过半个字。
那以后,展三公子也没再去拜访过那间独草屋。
他也曾数次路过瓦片里,每次都是隔着一条街,远远看见秋囡又在和乡邻少年们蹴鞠。
他总是看见秋囡的脚上仍然穿着那双大木屐,便猜到那一双难得的布鞋,竟被她当作宝贝收了起来,完全没派上用场。
他没奈何,只得暗自叹息。就在这一次次的叹息声中,秋也渐渐深了。叶落满地,日复一日都作了黄尘。
十月的时候,汴梁城的叶已落尽,这时候展三公子已不在京城。
深秋的黄昏,古道上扬起风尘,枣红马儿驮着满脸疲惫的展三公子遥遥直奔淮南官驿的大门。
驿丞带了众人出迎,亲身牵了马儿道:“展大人此番离京公干,一路可好?”
展三公子下马抱拳道:“展某公事在身,睡上一夜便要走,多蒙关照了。”
他确系离京公干,肩上担着一桩非比寻常的公事,因此一路小心,不到万不得已,宁可不合眼的。
就算是铁打的人儿,也吃不消这般干熬。为了睡这一觉,他特为多绕了十几里的路,专落在这江淮最大的官驿,就是为了“稳妥”二字。
展三公子果然倒头便睡。
他刚刚睡熟,这号称万全的官驿房中,便有一条诡谲的影子闪过。那影子是墨黑的,仿佛是从墙缝儿里渗透进来,无声无息飘上了大梁。
那影子用双脚勾住屋梁,倒挂着打量睡在床上的展三公子,影子的一只手,突然伸到了自己的背后——
展三公子就在这一刹那猛地睁开两眼——同时,他的手掌握住了枕下的剑柄。
他却没有拔剑。因为就在下一刹那,他已看见了影子从自己身后拿出的东西。
那是一个磨得亮光光的大铁壶!
“长慧大哥?!”展三公子坐了起来,“此地距东京千里之遥,你怎么……”
梁上的黑影拉下了蒙面布巾,露出越人长慧的脸。长慧倒挂梁上,向展三公子晃了晃手中的铁壶,只说了一句话。
他说道:“此地不宜久留,速跟我走。”
五、报恩人
展三公子偷偷牵了马,跟着长慧从后院离了淮南官驿。长慧发了急一样只是引着他走,也不说话。
两人默默走出约有四五里路,来到一处荒山野岭,长慧方才驻足,拾掇起一小堆生柴,点起了篝火,招呼展三公子坐在火边歇息。
他拨弄着火堆,开口道:“今夜官驿早有大敌埋伏,准要你的命。我杀了看守后院之人,才能带你出来。”
他说罢,遥遥一指来路,只见淮南官驿方向火光冲天,似乎成片的房屋都被烧着了。
展三公子犹如梦中,望着火焰喃喃道:“长慧大哥,你怎知道的?”
长慧道:“我一直跟着你。”
展三公子又道:“你为何要跟着我?”
长慧道:“因为我一直打算杀你。你曾杀了我的大恩人,我须得尽力给他报仇。”
展三公子大愣,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道:“我?”
长慧隔着一团跃动的红火瞪视着他,一字一字道:“就是你。”
他低下头,又拨了拨火堆,道:“太久了,或许你已不记得了。”
展三公子的脸色冷了下来,他慢慢道:“我是不是错杀过什么人?”
长慧冷笑了一声,道:“没有,否则你早已被我杀了。我从十个月前就开始盯着你,我们一家子千里迢迢来到汴梁,就是为了要你的命!”
展三公子怔怔望着他,忽然苦笑了一下道:“难怪你不愿结交我这个朋友。”
北风呜呜地吹着,那一团小小的火焰被吹得忽上忽下。深秋的荒野之中,连骏马都觉出了异样的寒冷,焦躁不安地刨着地面。
展三公子瞧着火焰,一直一直地沉默。
不知怎地,他忽然想起初见长慧之时,他那铁壶中酒的味道。
长慧道:“你大约是想不到,纵然大奸大恶之徒,也会有施恩于人的时候。”
展三公子叹道:“无论是谁施恩于你,都绝不会后悔的。”
长慧舒展了眉头,缓缓展开了笑颜。红彤彤的火光照着这粗豪汉子罕有的笑容,显得格外动人。他从裤带上取下大铁壶,在展三公子面前一晃道:“来一口。”
展三公子接过便饮。
那酒还如当初一样呛辣,仿佛幻化了水之外形的烈火,他以为自己吞得下去,不料饮得太急,嘴鼻内都如火烧,一口便呛了出来。
酒汁喷在火堆上,火焰高高地一蹿,又低了下去。
长慧大笑问道:“如何?”
展三公子抹着嘴道:“好酒!可让我糟蹋了。”说罢把酒壶抛还给长慧。
长慧接了,饮下一口,把铁壶拿在手中把玩,突然一手握住那细直的壶嘴,“唰”地一声,把壶嘴抽了起来。
展三公子清清楚楚瞧见了,那壶嘴下连着的,赫然是一枚奇形的小匕首。
是夜无月,那匕首在暗夜中闪着水银一样璀璨的光。展三公子知道,在酒里是泡不出这样锋芒毕露的利刃的,只有每日每夜细细地擦拭、打磨,它才能发出此时这般摄人心魄的寒芒。
谁可想见,那越人汉子每一夜在那破陋的独草屋中,坐在那三条腿的木桌旁,背对着熟睡的妻子儿女,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擦拭打磨这独特的匕首,然后再将它小心翼翼地藏在铁壶之中?
那大铁壶从不离他的身,正如他从不曾放弃过报人一份恩情的念头。
展三公子道:“长慧大哥,你一直是打算用这个结果我么?”
长慧道:“是。”
展三公子道:“那又为何救我?”
长慧道:“你是个好人,我不能眼看着你死在那些人手上。”
他说着,又晃了晃没了壶嘴儿的铁壶,问:“还要不要?”
展三公子大笑起来:“只要还倒得出酒来,我就要!”
他们像两个野人,在这暗黑无际的寒夜里,靠在火堆边你一口我一口地痛饮着铁壶中最后的残酒。
大铁壶隔着火堆抛来抛去,划过一道道银色的弧线,最后还是落回了主人的手中。
长慧业已薄醺,他站起身来,用匕首敲着铁壶,唱起那日在隋堤上的越歌。
他的歌声,竟比上一次听到时更添壮气,每一句都吐得铿然决绝,豪迈非凡。
展三公子仍旧只能听得懂头一句的:“今夕何夕兮——”
他知道自己若在此时发问,这越人汉子一定会将歌词相告。
然而他只是静静地听着。
这世上太多精妙的词,太多缠绵的歌。有些歌儿就算人人传唱,却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听懂?
今夕何夕,今日何日?
这一日,这一夜,这一秋山,这一荒野,可会是他俩之一的葬身之地?
展三公子笑了起来。他也有些醉了,但笑得更加开心。
他指着自己的头,对一曲歌罢的长慧说道:“某大好头颅在此,大哥若想拿了去,尽可一试!”
长慧向他点一点头,道:“拿不拿得了,我总要一试的。”
他将壶中最后几滴酒洒在火堆上,随即将火堆踏灭,纵身后撤,落在五十步开外。
展三公子也站了起来,他的剑一直都在手中。
两人静静站着,不知站了多久,连遥远处官驿的火光都已渐熄,周遭沉入浓浓的黑暗。
黑暗内,忽然有了一点极轻微的响动——就像是一片枯叶落地的声音。
连随风起——都是割面生寒的金铁之风。
间或有一两线寒芒闪现,倏忽而没,却又分不清是发自哪处,去向何方。
冬天日头出得迟,鸡啼了许久之后,山坡东面才隐隐有些发白。
又隔了许久,淡漠的曙色才慢慢浸染过来,照亮了坡上一个汉子,一位公子。
两人都已浑身汗透,显见疲极,长慧左手用力握着右腕,手中的匕首仍在不由自主地颤动。
展三公子握剑的姿势看来很稳,只是前襟临近颈子的地方,衣衫已绽开一条长长的裂口。
两人仍旧浑身紧绷,大睁着满是血丝的双眼,瞪住对方每一丝的移动。
良久,越人长慧的眼神忽然黯淡下去,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像是怀着毕生的遗憾,他深深地叹息道:“我杀不了你。”
然后他全副的精神仿佛都随着这一声叹息而瞬间老去,他整个人都软了下来,慢慢坐到地上。
展三公子浑身一松,也即时跌坐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长慧低着头,用力把匕首插进土里,闷闷半晌,道:“你的把势好,我杀不得你,问罪杀头,也无话说。”
他猛抬起头,道:“你知道么,我阿女不是个哑子。我怕她的把势藏不住,才要她……这件事,跟我的一家人都没有关系!”
展三公子忽然笑了。他摸了摸前襟的裂口,喷出一声笑,挣扎了一刻,才勉力爬了起来去牵马,仿佛全没听见这话一般。
经过长慧身旁的时候,才用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回汴梁再见了,长慧大哥。”他长长呼出一口气,跳上马背,很快便走得不见了。
后来……
后来的日子,也是这样的过。
瓦片里的穷街坊都知道了,打南边来的长慧一家在京城落地生根。这户人似是遭过什么大难般,来时穷得家徒四壁,全靠长慧在城里四处找活,长长短短地卖些力气。长慧人实诚又肯干,家里渐也过得安稳起来。他的一双儿女伶俐可爱,穷街坊们见了也都爱惜,但有余就帮着接济,拉扯他们一天天长大成人。
都说阿海像爹,长到十三岁上便有一身好力气,也能帮着长慧做活了。
秋囡仍然爱在小巷内玩耍,即便独自也能耍上好一会。她的性子却较古怪,人们都猜是她打小曾长了哑病的缘故,到大也不爱言语。
不过最让街坊们津津乐道的,还是这个小姑娘哑病治愈的过程,那简直犹如书本中的传奇——
那一天孩子们正在玩耍,有个锦衣带剑的年轻武官与歇了工的长慧一块儿出现,来到这瓦片里。两人肩并着肩,就一齐站在街那头笑咪咪地观看。那从来不会说话的小哑女突然冲过大街,欢欢喜喜地看一看父亲,然后拉住那武官。
接着,连街这边的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听见了,她用糯生生的南方口音,大声唤了那人一句:
“阿叔。”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