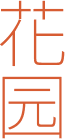作品:曾经的秘密海盗生涯
1.
那是我一生中最坏的时光。
疲惫,颓丧,独自蜷缩在狭小的阁楼里,预备在连绵的阴雨中挨过整个寒冷的春天。直到有一天,一个军官模样的男子敲开我的房门。
“我是索维尔上尉,”他向我敬礼,然后摘下帽盔,“很抱歉打扰您……的休息。”
他显然看出了我的怀疑和紧张,局促地笑了笑:“我来是想请您帮个忙,以私人的身份。”他朝门外指了指,“我听说,您是一位作家。”
作家?我皱了皱眉,并没有否认。
于是,这位索维尔上尉向我说明来意:他想请我为他的父亲写一部传记。
“他大概没有多少时间了。”军人面色凝重地说,“我知道他想留下一些值得记忆的东西……所以请您考虑一下,不管您是否同意,都非常感谢。”随后,他重新戴上帽盔,敬礼,离开。
作家?我不知道旅馆的老板对人们说了什么,这世界上有哪位作家会蓬头垢面地躲在不为人知的房间里,脸上挂满消沉和迷茫?他们不是应该在城市的大街上悠然漫步,接受少女们热烈目光的献礼吗?或是在觥筹交错的宴会上优雅起身,朗诵一首令人陶醉的诗歌?再或者,是在图书馆高大的书架间徜徉,无意间发现一本署着自己姓名的巨著……而我所有的只不过是一箱旧稿纸和一叠退稿信,它们宣告,在这有限的一生里,我的名字永远都不会出现在某本书的封面上。
所以我来到这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放弃不切实际的梦想,开始另一种生活。然而就在我开始适应这新的现实的时候,却有人希望我这位“作家”为他写作。这也许是生活对我的嘲笑,但不知为什么,当他说出“作家”这个词的时候,我却没有否认。
傍晚已经来临,楼下小酒馆里的喧闹声渐渐密集起来,透过地板传到阁楼上来。我摸摸口袋里寥寥可数的几个铜币,无奈地笑笑。
好吧。何乐而不为呢?
这位索维尔上尉的父亲,想必便是这平凡的小镇上一位不知名的老人,穷其一生也许都没有任何值得荣耀的作为,更不要说有人会为他写一部传记。而我恰恰是一个写不出真正著作的“作家”。也许不久以后,我就会欣然接下撰写生日贺词或是墓志铭的活计,凑到楼下的木匠和屠夫中间,喝上一杯麦芽烈酒,心满意足。
2.
两天以后,索维尔上尉再次找到我。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这样就太好了。”他露出宽慰的笑容,“我今天就带您去见我父亲。”
我跟随他来到一所靠近湖畔的老房子。和这里所有的房屋一样,它有着红色的屋顶以及白色的木板墙,墙上的白色油漆在雨季中剥落,露出斑驳陈旧的木色。在踏进房门之前,军人停下来:“父亲不知道传记的事情,我只是说请来一位医生……”
“我以为写传记是老人家自己的意愿。”
“是的,他以前说过希望死去之前能留下一些不会轻易磨灭的东西。但是我不想让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无论如何请您不要透露。”他的目光恳切。我只有点头,和他一起走进房子。
走上一道狭窄阴仄、吱呀作响的楼梯之后,我看到了老索维尔。他的房门敞开着,背后的窗户透进薄薄的光,把老人的轮廓变成一幅剪影。他坐在椅子里,似乎披着一条毯子,我看不清他的脸。
一位护工模样的女子从房间里走出来,向我们致意。
索维尔上尉走到老人身边俯下身:“父亲,我请来了这位——”
“艾布纳。”我说。
“艾布纳大夫。”
“我不需要。”椅子里的老人语气生硬。
“艾布纳大夫和别的医生不一样,”做儿子的劝慰道,“他会让你好起来的。”
老人沉默了片刻,语气更加坚决地说:“让他走。”然后便不再说话。
索维尔上尉回到走廊,有些尴尬地看着我。
“好像心情不大好。”我说。
“偶尔会这样,”他有些含糊地说,“只能慢慢来了。”说着,他朝门边退了两步,站到从屋里看不见的地方,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币:“这是预付的一部分……我的探亲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以后的事就多拜托了。”
我回过头朝屋里看了看,护工模样的女子正把药片和水杯端到老人面前。而老人的儿子则再度恳切地看着我,坚持把银币递过来。
“无论如何请您收下吧。”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这可能是家父最后的愿望。”
“噗”——老索维尔用力吐出了嘴里的药片。那枚药片弹跳着滚出房间,沿着楼梯一直滚落下去,发出哒哒的声响。
3.
后来的五六天里,我没有再去过老索维尔的房子。也许是因为第一次不愉快的见面,也许是因为不知道怎样扮演一位“大夫”,每当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总是对自己说“再拖几天也不算迟”。
上尉离开之前告诉我一些关于他父亲的事:老索维尔出生在湖畔镇,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里。他受过必要的教育,正直能干,曾做过湖畔镇卫队的副队长。退休以后他就在这所老房子里静享晚年,直到现在。
这样几句话似乎就已经概括了老索维尔平淡的一生,但对于一部“传记”来说显然远远不够。他儿子付给我的银币已经换成了一个季度的房租,以及口袋里几十枚哗哗作响的铜币,而我似乎也该为自己的第一份正经工作做些什么了。
再度造访老索维尔的家,那位叫做黛西的女护工带我来到楼上的房间。索维尔依旧披着毛毯,无动于衷地面朝门口坐着,我不知道他是否注意到我的出现。
“艾布纳大夫来了。”黛西说。
“我不要大夫,让他走。”
“难道您不希望早点好起来吗?”我说。
他沉默了片刻,把目光移向一边。“没有用。”
大概是上尉向黛西说明过我的来意,她拉来另一把椅子让我坐下,然后走去准备老人要服的药。
“索维尔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服药的?”我尽量让自己显得像个真正的医生。
“去年。”黛西稍微回忆了一下说,“去年他患了中风,右半边的身体不灵便了。大夫——之前那位大夫说病情不算很严重,是可以恢复的。”
“合理治疗的话的当然是可以的。”
“开始他还是肯配合着做一些锻炼的,”黛西倒了一杯温水,把药送到索维尔面前,“但是后来慢慢就不肯了,到现在一步也不肯走。”
老人张嘴接过黛西递来的药片,用力撇着下唇,松弛的脸颊把嘴角拉成夸张的向下的弧线。
“您应该尽量配合治疗,”我认真地说,“要相信医生的话,会好起来的。”
“噗”——老索维尔用力吐出嘴里的药片。这一次,已经开始融化的药片滚过膝上的毯子,落在他的脚边。
就这样,我连续几天去看望索维尔,却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回应。他故意做出的冷淡表情下面透着一股愤怒,在这怒气的驱使下,他像顽劣的少年一样,做出种种逆反的行为——吐出药片,掀翻茶盘,拒绝交谈和帮助。我不明白是什么让他如此不满,以至在这种格外需要照顾的情况下,与身边的人发生种种不愉快。
日子一天天过去,酒馆里的酒客们开始谈论雨季就要结束的话题,甚至为雨季结束的日子打起赌来。而我则为这一季即将结束而感到烦闷,或者说了无期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蜷缩在狭小阴暗的房间里,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便是写下一个倔老头的生平琐事。而每每看到手头廖廖十几行的笔记,我都越发觉得写出一部传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多地去到索维尔那里,和他说话,无论他是否对我的到来无动于衷。
这一次,我照旧在索维尔的茶桌旁坐下来,他坐在小桌的另一边,侧过头来看着我。我看到桌上靠近我的地方摆着一大杯水。
“这是给我的吗?”
他点点头。我仔细看过杯里的水,清澈透明,但靠近杯底的地方却沉淀着一层细小的白色颗粒。
“这是什么?”我敲敲杯壁。
“什么都没有。”索维尔说,“清水。”
“是盐吧?”
“我说过你骗不了艾布纳大夫的。”黛西走过来拿走了那杯浓得无法完全化开的盐水。
“是糖,”索维尔嘟哝着,“我说是糖就好了。”
然后,我看到他的嘴角向两边拉长、提起,眼睛眯缝了起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错觉——他笑了。
索维尔开始接受我的到来,偶尔会和我说话。甚至有那么一两次,他竟然同意和我下棋,尽管中途便捏着棋子昏昏睡去。虽然有这些小小的改变,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沉默地坐在那里,独自出神,或者混沌地睡着;仍然以恶劣的态度抵制服药,生气的时候用力地撇着下嘴唇。
我觉得自己搞不懂这样一个人——性情直率而倔强,不会轻易服输,在逆境里也应该会表现得比常人更坚强才是。而索维尔却好像在努力避免康复的可能,甚至当他察觉到我并没有对他进行实际的“诊治”时,反而显得友好起来。
偶然的一次,我注意到墙上积起的灰尘呈现出一些大小不一的方框形状。
“这里曾经挂过东西吗?”我问黛西。
“是些镜框。”她看了看那面墙壁,“索维尔先生叫我把它们摘下来了。”
“镶的是什么?”
“是一些嘉奖状还有勋章之类的,”黛西说,“索维尔先生年轻时的东西。”
索维尔先生年轻时。
我发觉自己从未想象过老索维尔年轻时的样子,甚至下意识地觉得他从来便是这副模样。“年轻时”——这个字眼让我意识到索维尔的衰老。我突然理解了之前所不能理解的种种,关于他的愤怒、冷漠,以及那些自相矛盾的顽抗。
那不是愤怒,而是恐惧。
他知道自己已然老去,即便康复,留下的仍然是有限的时光。那才是一切痛苦的根源——透过病痛,他看到了死亡的阴霾。没有谁能帮他分担这种痛苦,没有谁能够抵抗这种力量。一个人能有多坚强?当他明明感受到那一刻的临近,却又无法预知它的到来。也许只有不去直面才能减轻他的恐惧,然而人们却又在不断地提醒着他,以关怀的名义。所以他无法信任身边的人,对他们发怒,同时又以愤怒来掩盖自己的恐惧。人们在对他好言相劝的时候却并不知道,他需要的其实并不是这些。
我仍然经常去到索维尔的老房子那里,有时交谈,有时和他一起默默地坐着。就这样,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个寒冷多雨的春天。
4.
天气渐渐变得温暖晴朗,阳光终于拨开云雾,照耀着平静的湖水和赤红色的山脊,小镇上人们的心情也随之变得轻快起来。旅馆的女主人在门边开辟的小花圃里已经开出明媚的花朵,我请她将其中的一株移到花盆里,把花带到索维尔那里。
索维尔很不情愿地在黛西的搀扶下从椅子里站起来——如今站立和走动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很费力的事情——看着我把他的椅子调转半圈,挪到窗前,推开那扇久未打开的窗户。
阳光斜斜地从窗子里照进来,带着湖水气息的微风吹在脸上。索维尔和我坐在窗前,面对着窗台上那株随风摆动的橙黄色的小花。
“那年止水湖涨水,就是这样的夏天。”索维尔缓缓地说,“街上都漫着水。大人们在抢救谷仓。”
我转过头看着他,索维尔的眼睛眯起来,平日里混浊的目光似乎被某种温和的光芒所代替。
“我在街上走着,光着脚,水有齐腰深,妹妹在一只大木盆里。”他慢慢地抬起左手,用很小的幅度比划了一下,“她发着高烧,我推着她,漫无目的地走……”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追忆昨夜的一个朦胧的梦。
“后来呢?”
他没有回答,只是痴迷地看着细小的花朵在微风里跳舞,而后渐渐睡去。
此后,索维尔偶尔会说起一些往事,都是些很短的片段,其中大多来自童年和青年时代的记忆——也许人们的确会对更早时候发生的事情印象更加深刻;即便是这样,这些记忆的片段也会出现失真,甚至当他重复说起某件事情的时候,有些细节会有所不同——到底是吉姆还是卡特抢走了玩具?美丽的姑娘究竟是身穿蓝裙还是红裙?——然而在索维尔的脑海里,连这些不准确的回忆也在慢慢地变得更加模糊、前后颠倒,有时他甚至不肯承认自己说过的一些话。他更多地在讲故事的时候睡去,目光变得更加迟滞和茫然。
我只能尽力将这些回忆的碎片记录下来,按照时间顺序将其一一归位,像是穿缀起一串散落的珍珠。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与时间争夺那些记忆,如果不能尽早记下这些故事,它们就会被沉入时光的湖底,最终变成无法拾起的细沙。那些细沙之中不知已沉积了多少人的记忆,它们无非是些生活的琐事、不值得纪念和传诵的故事、必然被抛弃和遗忘的生命中的尘滓,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融,回到它们原本开始的地方。而索维尔的记忆却在最后的时刻被打捞起来,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
5.
我的笔记已经有了厚厚一叠,如果把这些零散的故事串起来的话,应该也会有可观的长度了。在这段时间里,上尉寄来一封信询问传记进度的事,并且在信里附上又一枚银币。我想这也许是他太过于急切地想要替父亲完成心愿,当然更可能的是,他越加为担心父亲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我的感觉却有所不同。与索维尔共处的这段日子,让我产生某种恍惚的感觉:明知道一位病中的老人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期待,但每当在他身边的时候,却会有种一切都不会结束的错觉。就像在长夜里守着一根即将燃尽的蜡烛,当你盯着它微弱的火焰时,却会以为它可以就这样一直燃烧下去。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残年,每一天都在走向结束,每一秒却又格外漫长。
有时我会觉得,这也便是我自己的残年——离群索居,了无生趣,放弃了心中的梦想和期待,这样的日子不知到何日为止。我是否真的有勇气放任自己的人生,让它如此这般继续下去?或是终于有一天可以收拾心情,重新开始呢?
我站在楼梯下,听见他的声音从卧室里传出来,这不是平日里的牢骚或自言自语,而是喊叫的声音。我加快脚步走上楼去,最先感受到的却是扑面而来的异味。索维尔坐在床上,瞪着站在床边的黛西,每当黛西想要开口说话时,他就会发出阻止的叫喊。
“艾布纳大夫,你可算来了。”黛西的脸上露出委屈和为难,“索维尔先生把裤子弄脏了,可是他无论如何不肯让我帮他换。”
我立刻明白了那股异味的由来——索维尔失禁了,这是衰老的又一个症状。他显然不能接受这件事,眼里露出慌张和羞耻的神色。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肯让黛西接近自己,当然更不可能让她见到自己裸露出身体。
“索维尔,”我接过黛西手里的衣物,“我来替你换裤子好吗?”
索维尔犹疑地看着我。也许是因为过度的紧张和激动,此时的他显得有些神智不清。
我俯下身靠近索维尔,他突然抬起没有瘫痪的那一侧手臂挥动了一下,虽然幅度很小,但非常用力。“不!”他吐字有些含混,但声音很大。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指了指黛西,“你总要选一个。你要谁给你换?”
索维尔的目光在我们两人之间移动了几下,像是在看着两个不能信任的陌生人。最后,他小声地说出了一个名字:“玛丽安。”
“你说谁?”
“玛丽安!”他提高了声调,清楚而坚定。在看到我和黛西迷惑的表情之后,他似乎更加着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名字,显得更加激动,仿佛哭闹的孩童呼唤着自己的母亲。我和黛西不知如何应对,手足无措。
这样混乱的局面一直僵持着,直到索维尔精疲力竭,终于安静下来。在我们为他擦洗身体、换上衣裤的时候,他尽管仍有不满,但已经无力反抗。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索维尔疲倦地躺在床上,半阖着眼睛;洗过的衣物与床单挂在窗口,默默地滴着水。空气中仍然飘着淡淡的异味,与房间里潮湿的气息混合在一起。我感觉它们似乎正在慢慢地渗进老屋的墙壁、地板,晕染着褪色的桌布和窗帘,最后终于融入黯淡的时光中。
几天之后,上尉回到了镇上。从黛西口中,他得知了这件事。
“非常抱歉,麻烦您了。”上尉对我说。
“玛丽安是谁?”
上尉脸上的表情出现一丝微妙的变化,他回头看看独自坐在床脚的老索维尔:“是我的母亲——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
一时间,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默默地点头。
这是一个太显而易见的答案,我却没能猜到。这或许并非由于我的愚钝,而是因为在我的生命中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人——那是他最信任的人,是他在失去尊严和保护的时候唯一能够依赖的人。除此之外,再没有谁能够真正安抚他的心灵。
上尉只停留了短短两天就离开了。临行前他向我说明:他很快就会调动到暴风城卫队供职。他决定安顿下来之后就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以便更好地照顾老人。
“传记的事情,就拜托了。”上尉有些忧郁地说。
“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我说。
上尉走后,黛西开始整理老房子里的物品,把不常用到的东西都打包起来。索维尔渐渐变得更加寡言、迟缓,越来越少坐到窗子那里去,只是在我和黛西的合力帮助下坐起身来,默默地倚在床边。他总是半垂着眼帘,鼻息粗重,往往让人分辨不清他究竟是睡是醒。他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不快,而像是已经接受现实一样默默地等待着某个时刻的降临。
“你是谁?”有一天他对我说,面带茫然地坐在床角,身上的衣服肥大松垮,像披着一条毯子;说话的时候,下颌与嘴唇在不自觉地颤抖。
“我是艾布纳。”我在他身边坐下,把手放在他的手上。他仍然茫然地看着我。
“我是你的医生。”我说。
“你不是医生。”他缓慢地摇摇头,转过脸去不再看我。
他或许真的没有认出我,我并未对此感到惊讶或遗憾。对于一个正在一点点丧失记忆的人来说,最先忘记的便是那些最近发生或是最不珍贵的事物。他已无法辨别我的相貌和声音,连名字的印象也不能留存。在回忆我的过程中,他的神情那样茫然,但在否认我的身份时,他却连一秒钟都没有用。这究竟是他随口说出的话,还是他早已知道事情的真相?我无从分辨。
也许,人的一生就是一段开端与结尾遥相呼应的旅程,那些在生命之初一点点学会的东西,最终都不得不重新归还给生活。直到一个人将所有的一切归还干净的时候,他便最终从这世界上湮灭殆尽。
我不知道在他的记忆中究竟还留下多少东西。他开始变得像一个婴孩,放弃了用语言表达自己的需要,而是代之以无意义的呻吟或是叫喊;他渐渐忘记了如何穿衣、如何起床,如何行走;甚至有一次,他在发怒的时候直接用松动的牙齿咬了黛西的手臂。
“你为什么要这样!”那一天,面对着仿佛野蛮婴孩一般发怒的索维尔,黛西惊讶而又委屈。她紧紧捂着几乎被咬破的手臂,负气地流下眼泪。
索维尔怔怔地看着哭泣的黛西,良久之后,他夸张地咧开嘴巴,发出并不悲伤的哭声。没有眼泪从他混沌的眼中流下来。
就在那一天,第一枚黄叶在不期之间飘落在索维尔的窗口。
6.
天气真正变得寒冷之前,上尉回到了湖畔镇。他整理了已经打包的物品,预备带走的必需物品只占了马车里不到一半的空间。
“我在暴风城找到了一处不错的住处。”上尉对我说,“那边的气候好些,条件也便利些。”
“也许有利于他的康复。”我说。
“说到康复……”上尉叹了口气,“我只是希望他好过一些,我也能感到心安。”
我们说话的时候,几个小伙子正在帮忙将坐在椅子里的索维尔从房间里抬出去。索维尔神情紧张,不停扫视着房间里的人,紧紧抓着椅子扶手。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到我站在那里、是否认出了我。
他没有发脾气,没有抵抗,没有叫喊,只是在经过门口的时候徒劳地用手抓住了门框,但很快就无力地松开了。我知道,他不愿离开这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我和上尉站在湖畔的老房子门口,风从我们身旁吹过,刮动马车一侧的门,不停地打开又关上。索维尔默默地坐在车厢里,垂着眼帘,似乎昏昏欲睡,又好像陷入了其他人无法进入的沉思。每当车门被风关上的时候,他的脸便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这是我在暴风城的地址,”上尉交给我一张字条,“如果需要什么帮助可以联系我。”他顿了顿,“如果传记完成了也请马上寄给我。”
“会的。”我点点头。
临行之前,上尉交给我一只不大的提箱。
“是家父给你的。”他说。
“这是什么?”
“一些旧物。”上尉回过头,看了看马车的方向,“父亲坚持一定要由你……他请你好好保管它。”
我从上尉手中接过提箱,目送他钻进马车,驶向镇外的大道。
7.
我打开那只老旧的提箱,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一样一样在眼前摆开—— 一张不很传神的图拉扬将军的小幅画像,几幅镶在画框里的奖状,上面用朴素的字体写着:“奖给杰克·索维尔上尉”。
这是索维尔留给我的纪念—— 一个人的梦想和骄傲。它们曾经挂在他的墙壁上,作为他对年轻岁月的缅怀;又在他衰弱痛楚的时候被锁进记忆的角落。我曾在索维尔的墙壁上看到它们留下的尘迹,也正是因为这些尘迹,才开始了解到它们主人的内心世界。
然而在这一刻,我突然不敢确定自己真的了解过索维尔——衰老和病痛究竟剥夺了他的全部理性,还是以另一种方式赋予了他不同的智慧?我常常认为他已经不能判断寻常的是非,但又在某一个刹那,他又会让人觉得他已经洞察了一切。
也许,他知道,一切。
我突然醒悟,我正和曾经的索维尔一样,在以一种貌似坚强的姿态逃避着生活的真相。离开熟悉的地方,锁起过去的文稿,放弃写作的梦想——我曾以为这种放逐的仪式可以使自己忘记那些羞耻和悲哀,但事实上这却不过是一场负气出走的把戏。若是真能放弃,我为何不舍得毁掉那些文稿,又为何不否认“作家”的身份,甚至,没有拒绝这份与“写作”有关的工作?或许,在我自己都未能看到的灵魂深处,那个旧梦仍然是幸福的、美丽的,是我唯一想要到达的天堂。
冬天来临的时候,我再次收到来自上尉的信件,得知了索维尔去世的消息。虽然已经预料到事情的发生,但我还是为它过早的到来感到有些惊讶。从上尉的信中得知,去世前的那段日子里,索维尔已经非常衰弱,不再与身边的人做任何交流,最后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从字里行间,我看出了上尉的悲伤和遗憾,但最后一段共处的日子还是带给他些许安慰。
“至少,我算是尽到了一点做儿子的责任。”他这样说。
尽管索维尔在去世之前并没有看到自己的传记,但上尉仍然委托我把传记完成。这样一部传记也许将成为他哀思的寄托。我甚至猜想,这件事从一开始便只是上尉对父亲的误解——为倔强、要强的父亲留下一些所谓的属于他一个人的、难以磨灭的痕迹,是他能够寻找到的一种安慰,是在最终的时刻都无法真正理解父亲的一种释怀。这种猜想一度使我不愿草草动笔,但我终于为写作这部传记找到了新的理由,也是真正的理由。
我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写作——专注地回忆,真诚地思考、忠实地写下那些从心中流淌出来的文字,关于时光,关于情感,关于生命。
杰克·索维尔,我该如何描述这个人的一生?
他只是芸芸众生之中最平凡的一员,是茫茫沧海之中最微小的一粟;是造物主遗落在宇宙里的一颗尘埃,偶然地映射出一点微茫的光亮。在短暂而又漫长的岁月中,他体会过脆弱、恐惧和悲伤,也拥有过梦想、欢乐与爱;在孤独而又熙攘的旅程中,他试图抹去或是保留的一切,最终都将被时光磨灭成灰烬,并与这世界一同永存。
他是我们每一个人。
8.
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我收拾好行囊,踏上旅程。
临行前,我将传记的初稿寄给索维尔上尉,并附上两枚银币——它们来自于那只盛装旧书稿的木箱,以及冬季里作为家庭教师所获的酬劳。我确信自己无需为这部传记索取稿酬,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最宝贵的馈赠。
我庆幸自己曾用如此短暂的时间陪伴过一位老人,与之共同度过他人生中最后一段有意义的时光。在短暂的相逢之中,我们的足迹偶然地交织在一起,它们如此浅陋、凌乱,却最终成为镌刻在我生命之中的纹理,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