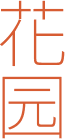作品:火星哲学家
“那是七十年代刚开始,我眼看着我们的朋友David,变成了另一个人。——等等,那玩意儿确实关了吧?我可不想接着要说的话被其他人听到。
“很好,让我们继续。
“熟悉?我当然熟悉他,我认识他的时候,George还没把他那只眼睛打瞎呢。——好吧,没有全瞎。用他的话说,是‘非常模糊(very hazy)’。那时他并不像后来的样子,是那种你很愿意领回家,你爹妈也很放心你和他玩的小孩,又整洁,又有礼貌。
“人们都说变化不是突然的。说他为此准备了十年,不断尝试各种风格,突破自我,直至奇迹降临;说他深思熟虑、精心策划,就像一个艺术家创造一件他预感会不朽的作品,就像一个学者钻研某种他知道将改变世界的理论;说那是非凡的天才灵感和长期的思索、痛苦、渴望和碰撞的产物,影响了整个世界和一个时代……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屁话,后来连他自己也这么说起来。
“但如果你是一个像我这样的朋友,就会知道这都是鬼扯。他过去十年的折腾,和他后来成为的那个人,几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至少我看不出来。事实上,没有任何征兆地,在极短的时间里,‘砰——’他变成了另一个人。
“忽然之间,所有人都在议论他的样子:首先,他那时候非常非常白——可不是你妹那种透着粉红的雪白,而是像漂干净的骨头或是月光一样透明的苍白;还有他的头发,那种橘红色——可不是你妈的头发那样带着金色或棕色的所谓橘红,是我见过的最鲜艳最轻盈的橘红,像火,又像我们小时候听过的故事里狐狸的皮毛。——什么?你说他染头发和化妆?老天啊,他当然要染头发和化妆,不然怎么解释自己变成了那种模样?
“如果你看过他后来的样子,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尽管他仍然在坚持,看上去也似乎是同样的造型,但你能清楚地看到他发根露出的金褐色——那是他头发本来的颜色,还有他的脸上的苍白和疲惫。那时他的样子和之前又完全不同了,不,我没法形容,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是一个有什么降临到他身上,又把他搞得支离破碎的人的样子。
“毒品?你是说毒品吗?
“不,不用道歉。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时候他开始吸毒,吸得够狠的,也许太狠了,吸得就像一个眼睁睁看着自己一生心血付诸东流的人;一个极其突然和悲惨地失去了毕生挚爱的人;一个满怀信心拥抱这个世界,却被世界一拳头打在鼻子上,又一脚把他的脑袋踩进泥里的年轻人……是的,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他糟透了,虽然他努力让一切看上去还算OK,可我们都知道他差点死掉。每个人都对他说,嘿,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看上去简直他妈的就是个死人了。但是他说——有那么一次,他对我说,他只是想活下去。
“时不时的,他会找我喝一杯。我们是这样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俩认识,交情不错,但不知道我们常常单独见面,说一些平时不怎么对人说的话,一些要么太蠢、要么太疯,要么太恶毒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吧?每个人都该有这样一个朋友,因为每个人肚子里都搁着这样一些话。
“他说:我只是想活下去,并尽量不要发疯。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了,要说再见实在是太痛苦了,这太难了,爱人,这对我来说太难了。——他总是把人叫作‘lover’,这是他的习惯。但我并不是他的lover,这点一定要说清楚,从来不是,我们只是朋友。
“他说:我知道会很痛苦,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痛苦。而我必须从这样的痛苦里活下去,并竭尽全力不要失去理智。
“我说:但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我的朋友。如果这么痛苦,那你为什么不继续扮演他呢?去啊,去继续巡回演出,去继续出新的歌和新的专辑。你们至少还可以再走红五年、十年,甚至更久,大家都这么说。反正你总归是要扮演某个角色的,这就是你的生存方式。而且要我说的话,你实在是一个不错的演员。
“他说:不,爱人,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们都说我创造了这个角色,说我完美地演绎着这个角色,传达出这样那样的信息,表达着这样那样的情绪……有些说法简直让我瞠目结舌,我做梦和发疯时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深刻。
“但他们说的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有时候连我也这么以为了,以为他是从我的梦想、憧憬和欲望里诞生,是我的作品,是我灵魂和思想的结晶。我装作是他,装作用他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用他的灵魂来感受这个世界。就好像我和他一样来自太空深处,从未接触过人类这种存在;从未见识过一种如此奇特的智慧生物,以如此奇特的方式改变和创造这个世界,组织社会,发展文明,彼此相爱又彼此仇恨、伤害;从未感受过如此的美丽与丑陋、激情与麻木、喧哗与孤寂、智慧与愚昧……我想象它的震惊,它的激动,它的迷乱,它如何极力保持着观察者的冷静和理性,又是如何不可避免地被人类吸引、影响、诱惑……直至纵身跃入这光怪陆离的旋涡之中,选择了一个最奇特也最疯狂的身份,来拥抱这个世界,品尝这个世界,进而影响这个世界。
“它当然会成为摇滚巨星,它只能成为一个摇滚巨星。如果它在三千年前到来,会选择祭司或巫师的身份;两千年前,它会成为先知或哲学家,甚至是救世主;如果是一千年前,它会是神学家、殉道者,或是火刑架上的异教徒;哪怕它来到一两百年前,也会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启蒙思想家,甚至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它来的太晚了,我的爱人,太晚了。它来到我们这个时代,浅薄、虚荣、疯狂、混乱而又变化无常的时代,除了做一个摇滚巨星,它别无选择。
“我的爱人啊,你知道吗?从此我的每一首歌,都是它向这个世界的呼喊和宣言;我写下的每一行歌词,都是它发回自己星球的,一个地球观察者和游历者的明信片……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自己那一刻的感觉。我知道我的朋友变成了另一个人,一开始我就知道,但我从未看的如此明白。
“我看着他的眼睛。全世界的女人,还有一半男人为之疯狂的眼睛:一只是浅蓝色,我熟悉的那个孩子的眼睛;一只是深褐色——哦,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十四岁的时候,为了一个女孩,George揍了他,擦伤了他的瞳孔收缩肌还是什么玩意儿,所以他这只眼睛的瞳孔就一直在放大状态,让人觉得是深褐色,并且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但我十分确定,不管你信不信,我的朋友,那一刻我十分确定,他那只深褐色的眼睛也看着我,有谁,在用他那只坏掉的眼睛,好端端地看着我。
“那一刻我屏住呼吸,然后,我看着他的眼睛,浅蓝色的那只,我说:David,它还在,是吗?
“他说:是的,噢,是的。该死的是的!
“但是它必须走!他说:我不能再承受了,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太多了,太沉重了!你不知道它把什么样的画面放到我脑子里!你不知道它让我体验着怎样的精神和灵魂!你不知道有多么深远,多么广阔,又多么沉重,你不知道那是怎样的光明,怎样的黑暗,怎样无法形容的狂喜,又是怎样难以想象的悲哀和寂寞!上帝啊,我只是想活下去,并竭尽全力让自己不要疯掉……”
(短暂的沉默。)
“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先是法国、再是纽约、然后是柏林、瑞士、京都……他活下来了,没有发疯,还戒了毒。他干得不错,真的不错。我得说,我为我的朋友骄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从那样的情形中存活下来,并始终保持理智。
“人们对他后来的样子大惊小怪,因为他不再化妆,不染头发,不穿高跟鞋和长筒袜;后来他甚至开始练习拳击,对陌生人微笑,看上去和善又快活,和儿子的关系也亲密起来——这孩子被他教养的很不错;然后,像那些老套的故事,他遇到一个年轻女人,爱上了她,我们都参加了婚礼,伴郎就是他儿子;他后来的合作者抱怨他太恋家,一到六点就准时离开录音棚;啊,还有他可爱的小女儿,结果他成了我所见过的最痴心最傻的老爹,为了女儿他甚至去给动画片配音……你知道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发现他看上去非常像他去世的父亲,同时也非常像我认识的那个叫David的小男孩老了的样子。
“我从没对任何人说过。我是说,我要从何说起?我要怎么对人们说:嘿,你们知道吗?我的朋友David——David Bowie,你们都喜欢他,爱他,崇拜他,他这一生创造过许多角色,扮演过许多角色:Major Tom、Aladdin Sane、Halloween Jack、Thin White Duke……这些角色你们也都非常熟悉和喜爱。但你们有没有想过,有那么一种可能,其中一个并非由他凭空创造和扮演,其中一个,是真正来自未知的时间和空间,占据他的精神和灵魂,短暂地与他同在。
“在他创造和扮演的所有角色中,有一个曾真实存在——来自火星的旅行者和观察者:Ziggy Stardust。”
(轻微的噪音。)
“不是来自火星。”
“什么?”
“Ziggy Stardust,他不是来自火星。Stardust 是以S打头的,这表明他是土星(Saturn)殖民地的公民。”
“什么?!什么?操!噢——我是说,噢!天哪!……为什么David说他是火星人。”
“我们也很好奇。也许他觉得‘土星人Ziggy Stardust’听上去没有火星人那么酷?”
“好吧,你说服我了——这确实是David做得出的事儿。”
我从未想过摆脱他,Ziggy Stardust,我们开始成为同一个生物,同一个人。这时你会尝试各种混乱疯狂的法子,只为了从他之中逃离片刻……
于是你开始沉沦,开始迷失……是我创造了他吗?还是他攫取了我?我不再知道自己是谁,我的艺术成为我的生活之时,我的生活亦开始模仿我的艺术。
所以我对他说:必须结束了。我知道这是残酷的最终一击,但我必须如此。有时候你就是必须如此残酷,必须直面自己最爱的东西,自己创造的最爱之物,却说:不,我不再如此。
—— 大卫·鲍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