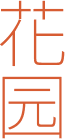作品:雪夜松谭
半夜下起了雪,到五更时,北风更紧,雪越下越大。掌柜的年纪大了,睡得浅,尽管寒意料峭,还是裹着他那领老皮袄,早早坐到柜台后,点起灯来,看看雪势,吩咐伙计把柜房前的腰厅收拾一番,抬进火盆,摆一圈桌椅,连外面院子里的长凳也揩拭干净搬进来,把窄窄的腰厅挤得满满当当。
原来这老掌柜颇有见识,看天色便知少则一日,多则三五天,江上不得开船,往来客人保不齐要困在这渡口。渡口虽有几家客栈,然本当离去的既被困住,只是行经的又要寻落脚处,必有客人无处安置,且将这腰厅拾掇出来,安排火盆灯烛,再备些酒水饭食,也是与人方便,也是赚点风雪钱。
果然才到下半日,厅里便满了,有人向火取暖,有人借来熏笼烤衣裳鞋袜,有人叫酒叫饭吃将起来,又有渡口卖零星吃食的、卖水烟的、卖杂货的、说书的、唱曲的,不顾天寒落雪,见此处热闹,纷纷趁了过来,又往里间客房窗下吆喝过去,客房里也有人开了门窗看热闹,一时间人来人往,进出乱串,四下浅酌低唱、吆五喝六,好不兴旺。
这风雪也来凑兴,直到傍晚,再没个停的意思。有那原本心存侥幸的客人,见渡江无望,只得寻下处踏实安歇。仍留在此间的,或是囊中羞涩,只索在这腰厅凑合;或是来得晚了,各处客房已满,无处可去,且先在此等候;也有那好热闹的客人,嫌客房阴冷,不如此处火光融融、人声喧哗,也不肯离去。老掌柜为人厚道,只叫伙计把火盆烧得兴旺,又多添了几盏灯,竟是一个“通宵达旦”的意思。
便有个器宇轩昂的老者,使手下小厮,招手叫伙计过来,与他两吊钱:“辛苦店家多添炭火,毋惜灯烛。”
伙计忙殷勤答应了,又去说与老掌柜。掌柜的赶紧从柜房出来,与老者见礼,只见他穿一件驼色库绸缺衿儿棉袍,罩一件灰色荷兰雨缎马褂儿,卷着银鼠袖子,头上一顶灰蓝色哆罗呢帽罩,看不出甚么帽子,有顶戴没顶戴,生着清瘦端正的容长脸,疏疏落落的花白胡子,相貌和蔼,气度不凡。一旁的小厮仆役也都衣裳济楚,只神色里带了些不耐。
老掌柜越发放低身段:“尊驾何来?可有下处?此间客房已满,得罪得罪!如不嫌弃,外头还有间更房,收拾出来勉强也能过夜。只是挨着马棚,气味未免冲撞了些,幸而天气寒冷,使店里上好的更香,紧闭门户,倒也不妨事,尊驾意下如何?”
老者连声称谢,一旁的小厮却说:“我家老爷素喜开阔,劳烦店家,有没更清净通畅的地方,权且给我们歇歇脚?”
老者便呵斥小厮:“出门在外,哪有那些讲究。”言语终究不是格外严厉。那掌柜的何等精明,略思忖片刻,便说:“既然如此,更房先替您老收拾出来,有个放行李处,或是后半夜乏了,略躺躺也好。后院还有个松棚儿,挂起厚棉帘子,烧上炉火,虽不如屋里暖和,却清净许多,您老且挪到那儿去休息可好?”
老者听说是“松棚”,便觉雅致:“如此甚好。”那伙计却把眼睛来瞅掌柜的,心说咱家店里何曾有甚么“松棚儿”?老掌柜也不多说,请客人少待,带着伙计忙往后院去了。
却原来后院有一个破棚子,原是砌的一个石台,后来支起四根柳木,上面又横搭着竹竿,铺了油布,正晾着砍来作柴火的松枝,犹带着松针,厚厚地搭在竹竿上。幸而大雪下了一天,院子里银装素裹,平日的腌臜破败处倒是一些儿也看不出来。
掌柜的一叠声地喊人,把石台上的雪清扫干净,铺上大棕垫子,再厚厚地码几层褥子,又取来棉帘子四面遮挡,并四个大红灯笼挂在四角,炕桌、坐垫、烛台、灯盏、小茶炉子、小盆景儿、铜火盆、竹熏笼从各个房间搜罗出来,流水似的搬来,伙计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这间“松棚儿”竟成了渡口一景,更是这店的招牌。——却是后话了。
那老者的小厮是个乖觉的,早跟了过来,见这松棚简陋不堪,又看他们一番忙乱,心下鄙夷,却不好说破,只叫人取来自家马褥子铺在上头,又拿出茶具和香炉,从荷包里掏出两块香饼子熏上。此时夜色渐深,风却停了,细细的雪花搓盐扯絮般自天际飘落,越发装点得这临时凑合起来的松棚儿如琼楼玉宇一般,四角的灯笼又将这一隅染上一层蒙眬的绯红。老掌柜还不知从哪里寻来一只半人高的梅瓶,立在一盏灯笼下,插着三两枝半枯的梅花。
老者一看便赞风雅,小厮塞块银子给掌柜的:“但捡洁净可口的酒食上一些来。”老者又说:“老人家若是不忙,何妨陪我坐坐,天气寒冷,人多些才暖和有趣。”
掌柜的再三推辞,老者只是坚请,还说:“我看前厅再无落脚之处,若是再有客人来,无处安置,也不妨请来此处,大家作伴也好。”
老掌柜心中疑惑,将那小厮扯到一旁:“如何你家老爷这般随和?倒叫小老儿不知怎么处才是。”
小厮便笑道:“我家老爷走南闯北,最喜村头巷尾闲话杂谈,如老丈这般见多识广、不村不怯,正与我家老爷作伴,长夜闲谈,岂不是好。”
这时偏有一角油布教松枝戳破了,棚子里的热气蒸腾上去,那雪水滴滴答答地漏进来,掌柜的忙叫人取大铜盆接水,又使人搭梯子往松枝上再铺一层油毡。老者袖了手,看他们忙乱,倒觉颇有趣味。
也是合该有事,前头腰厅里有个卖唱的年轻媳妇子,为人甚是乖觉,一直张着掌柜和伙计们的动作。这会儿悄悄摸到后面,趁无人注意,竟自掀帘进来,直往老者这边过来,先拜呀拜地胡乱行了个礼,又笑着问:“您老吃水烟?吃潮烟?听书罢?听段儿罢?《罗成卖绒线》、《大破寿州城》、《武宁关》……”老者纳闷:“这都是什么讲究?”掌柜的忙过来轰她:“你快出去!这不是你来的地方!”那媳妇子还不服气:“我晓得这位老爷是体面人,这不又没唱《大小姐骂姥姥》、《小两口争被窝》……”
那小厮闻言,忍不住扑哧一下笑出来,老者也掌不住笑了。掌柜的团团告罪,老者忙说:“不妨事不妨事,大雪天讨生活,怪可怜见的,若是有老丈陪着,过来烤个火歇一下,也是不妨的。”又叫小厮给那媳妇子一把钱。
那媳妇子这时却羞红了脸,拿过钱数也不数,掖进裤腰,陪着笑说:“您老心地好,我给您老唱个《青柳儿青》好不好?”
老掌柜这下心思更定,便说:“你也别唱了,去后头巷子看看孙娘子歇下没,没歇下请她过来,帮着整治吃食,沏茶烫酒。”又吩咐伙计:“去个说话明白的,看看西街上老宅子里郑先生可得空闲,一并请来陪老父母坐坐。”
他这里已叫上“老父母”了,老者连忙说:“不可不可,此地既非官场,老丈又不入公门,咱们萍水相逢,兴之所至,把这些‘父母官’、‘子民’的虚礼都去了罢。”那小厮一笑,提醒道:“我家老爷姓何。”老掌柜忙跪下行礼,口称“何老爷”,小厮赶紧架着他只不叫跪下去,又问:“老丈怎么称呼?”掌柜的就说:“小哥叫我老夏就得。”何老爷便道:“原来是夏老。”老掌柜忙说:“啊哟!这可使不得,老父母您是什么样儿的根基,我老夏算个甚么,怎好妄攀起来。”
正在这时,就听见外头一阵脚步声,有人隔着帘子笑道:“夏老还有这等雅兴,往日里我倒是把您老看俗了。”说笑间,帘子一掀,先进来一位道骨仙风的老先生,掌柜的却不认得,跟着进来的就是说话的这位,年纪轻一些,好文雅端正的相貌,正是掌柜的着人去请的“郑先生”。
但见那郑生满脸堆笑,进来振臂直前恭恭敬敬地与何老爷请安,又扶着那位老先生,对掌柜的说:“却是巧了,我家老师自京师回乡,路过此间,被我苦留下来,正逢上夏老襄此雅事,岂不是有缘。”老掌柜忙与老先生见礼,一边说:“郑先生就不要打趣小老儿了,小老儿知道甚么雅咧俗咧,与各位大人扫榻温酒而已。”
那老先生本有几分倨傲,待看清何老爷面目,忽然呀了一声:“何大人!”忙抢过来打了一躬,“一别数年,不意在此相遇!”倒把何老爷吓了一跳,仔细打量一番,才犹犹豫豫地说:“这是石翁不是?”
被叫作“石翁”的老先生笑着上前拉住何老爷:“正是老朽!当日高侍郎府上一见,何大人还记得否?一别数年,大人风采依旧!可喜可羡!今日何等有缘,竟于此穷乡僻地偶遇,三生有幸!”
那老掌柜是何等乖觉之人,郑生也是玲珑性子,见状一齐抢上前来,一个说:“二位竟是旧识,如此大妙,正所谓‘他乡遇故知’……”一个说:“既是老师的故交,莫若移步寒舍,虽不如此处雅致,也还有些许景致,待我做个小东……”老掌柜闻言,便拿眼睛去觑郑生,心说你这样截胡,也未免太不厚道。
何老爷忙说:“此处便好,也不甚寒冷,夏老辛苦张罗,我们就不要孤负了老人家一番心意。”那郑生虽如此说,其实他靠着祖上一点薄产,自家不事生计,又无心进取,惟好丹青书画,自命装点山林,外面看着还体面,内里已渐渐消乏,闻言便不再坚持,只帮着张罗何老爷和石翁先生安座。
这时又有人掀帘进来,却是一个家常打扮的妇人,穿条元青裙子,罩件月白袄儿,头上钗环全无,虽徐娘半老,但眉目开展,态度大方。见一屋子老少爷们,不侉不怯,垂下手来,安安娴娴地道了一圈万福。老掌柜便说:“这位孙娘子,原在大户人家服侍,造得一手好汤水,又懂得安席上菜的规矩,温酒沏茶的讲究,小店门面浅,人手粗,但有贵客往来,就请她来席间服侍。”孙娘子微微笑道:“夏老谬赞了,老爷们请坐,小妇人是乡间女子,不懂京城规矩,只行个怯礼儿罢。”说着又福了两福,拜将下去。何老爷忙说:“不要行礼。”又说:“途中风雪阻隔,蒙夏老盛情,与各位有缘,雪夜闲谈,都不要太拘束,也无须甚么伺候。”孙娘子道:“老爷既是京城里的大人,便同我们的衣食父母一样,该当伺候的。”说着就退到一旁,带伙计整治起酒食来,端的是手段娴熟、举止有度。石翁就点头叹道:“果然是‘宁娶大家婢’。”郑生咳嗽一声。孙娘子只作未听见,依旧微微笑着,手中不停。何老爷便来打圆场:“我等就当萍水偶遇,不拘俗礼,围炉夜话闲谈,有些什么放肆处,大家也不要见怪。”众人都说:“这样最好。”郑生且笑道:“若如此,何老爷算是遇着了。我这老师以书画优游公卿世家,见多识广,自不必说。夏老在这店里也有四五十年了,一肚子古记儿、笑话儿,只怕这雪下上三天三夜,也听他说不完呢。”
说话间只见帘子外似乎有人探头探脑,小厮问了声:“是谁?”孙娘子皱了皱眉,冲外头招手道:“阿珠,你来,帮我打个下手,不要生事儿。”
却是早先那个卖唱的年轻媳妇子,只敢在帘外逡巡,闻言才笑嘻嘻进来。原来这不多会儿,她竟重新打扮了,穿件桃红棉袄,套着水红衬衣,戴了条大红的领子,挽着同色的大红袖子,还系了条葡萄紫的裙子,挂着香牌儿、荷包儿,又掖着一条鹅黄色的绣手巾,花枝招展。终究不敢放肆,怯生生地行过礼,再不敢问抽水烟潮烟、听曲子段子了,忙挽起袖子,自去孙娘子身边搭下手。
一会儿工夫,孙娘子已把酒饭摆上,虽不过店里现成的白水煮鸭子、熬羊肉、焖猪头,自家做的腌腊,几样寻常瓜菜,一屉白面馒头,收拾得十分干净齐整,葱丝蒜末、醋碟酱碗,颇见心思。因天气寒冷,就着火盆架起铁篦子,一样样或是拿砂锅煨着,或是拿膛罐坐着,孙娘子又将一簸箕花生芋头埋进火灰里,并大锡壶里烫的黄酒,大陶罐子里煮的粗茶,香气袅袅,热气腾腾。
众人围炉坐了,何老爷自是上座,石翁作陪,郑生和老掌柜谦让了一番,方坐在何老爷右手,老掌柜就在石翁下手坐了,连小厮也陪在最末。何老爷还招手叫孙娘子并阿珠也来坐:“不要拘礼。”两人再三推辞,才搬了两张杌子,在一旁斜签着坐下,看觑酒菜火候。
一时间外头雪花飘飘、寒气萧萧,松棚子里却是炉火融腾、香气熏蒸、暖风微度、笑语时闻。究竟这一干人,于风雪渡口,因机缘巧合,围炉夜话,却是闲话些甚么,且听下编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