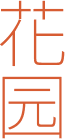作品:九万里
师兄们说的对,天下很多事情,是人力不可违的。
我用尽自己的三脚猫医药功夫,仍然止不住他伤口渗血。入夜后,他开始发低烧。我知道这是极不好的征兆,但束手无策。
“我背你去襄阳城,听说那里的医师医术很好——”
“我就是医师,医术也很好。”他提醒我,“你我已尽人事,剩下的只能听天命。少侠你不是要赶考吗,上路吧,不要耽误你的行程。”
我……
我是应该走的,再不走就赶不上开考了。
但我不能。
我在他身边坐下,“不走了。等你没事了我再启程。”
他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忽然开口,“若是少侠还有时间稍驻,能否帮我一个忙?”
这个像崖上凝雪一样的人,竟会开口求助。我立即拍胸,“但说无妨。”
他将刻刀递给我。“帮我把碑刻完。剩下的不多了,我来说,你来刻。”
我心头一空,看了眼他渗血的手腕。我明白,但凡还有力气继续,甚至还有恢复的希望,他都不会开这个口。
我推开他递来的刻刀,回身从地上捡起遥光,凌空舞了个剑花。
“你可算找对人了。我乃玄庚道人门下弟子。本门剑术高绝,斩金镂玉、劈柴切瓜无所不能,他派无能出其右者。雕石刻碑这种事,交给我就对了。”
他一脸惊异。我于是起手,一招“断云斩月”,雕完了他刻了一半的“薤白”。
说来也怪,这明明是我第一次用遥光,它却像长久以来就长在我手上一样,折转敛放,运剑自如。一瞬刻出来的笔画,竟然比他反复磨刻出来的还要精准深入。
我得意地看他,以为会听到“阁下剑术竟然如此高妙”“失敬失敬”之类的话,但他微微一笑,便开始忆诵药名,速度不缓。我急忙埋头苦刻,不得分心交谈。
师父一定不知道,直到此时此刻,我才第一次对习得剑术心生由衷感激。
他也一定想不到,他出难题让我送的遥光剑,成了我绝乱心境的救命稻草。
人行远途,方知大化。曾经的经历,终有它不可预知的意义。
待我气喘吁吁刻完那“剩下不多”的部分,已经是月上天顶。竹林在夏风中轻摇,筛下一缕缕通澈明流。
“刻一块碑,挺累的。”我喘着气,提剑看倚竹而坐的医师,暗示此时是不是该有句感谢。
他甚是不解人意,只又说了一个人名,让我刻在碑的末尾。
我咽下委屈照做了。刻完动念道:“这可是你的名字?”
“我叫孟莳。刚才让你刻的是我师弟的名字。他本是圣人西拓疆域时的随军医师,却最终为救两个回纥孤儿而死。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说,希望以后收他们为徒,传授医术。他无力阻止人战死,但可以把中原医术带去荒漠,让更多人知晓获救。这件事他终究没来得及做。我此行本想替他完成,但……好像也来不及做了。”
我默默听着,觉得嗓子堵得难受,很多话想说却说不出口,最后只是说:“先生还有哪些同门,我把这消息带给他们,也许他们能够完成。”
“没有了。”月光浸润他低垂的长发,顺着长衣流淌渗入身下广土,“我是本门的最后一脉。本门为山野医家,前代乱世中救人无数,在民间颇得声名。但现今已是太平之世,圣人立太医署,举一国之力编修药典,以官编药著统天下医言,弃僻药偏方。这固然是好事,让众多江湖骗术无空可钻,但是我们这样的人,也失去了依傍之所。门庭冷落是为大势,可叹,而不必悲。”
说到后来,他已经是气力不继。但我没有打断他,没有劝他休息。因为人世间有些事情不能歇止,一停下,也许就没有机会再完成了。
天道无常,世势流转。有的力量生,有的力量死,这些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师父孤执,装作看不见。两位师兄也曾经装作看不见,但他们最终在信里写下了“尽力相搏,终知大势不可违”。
我低声说:“同门既去,那我帮你。”
孟莳侧过脸看着我,苦笑,摇头。
“不必了。少侠你是识时务者。从刚才刻碑我就看出来了,你剑术根脉纯正,显然是得名师倾囊相授,自小打下深厚根基。但你既然一心赴考,这些传承就不再能左右你的人生。你与我们不同,不是陷在旧日罗网里的人。”
我突然觉得心里被深深刺了一剑,痛到无以复加。不,也许这一剑早就刺在那里,我只是像师父一样装作看不见。直到有人出语点破。
“先生……也怪我有负师门?”
“我并未怪你。人只一世仓惶岁月,无论怎么选,‘不负’只是妄语,得失更不容他人置喙。况且是否‘有负师门’,也并不只在是否接下师父衣钵。我那辞别远行的师弟,就比我更承一门之荣。”
我很感激他这么说。但是,那样的安慰,于我并不够。
今夜,我必须拔出那把剑,必须封之以鞘,不然今后向任何方向踏出脚步,于己心都只是歧途。
于是,我对着这个刚认识的陌生人,说出了那些封存心中的话。
“我父母都是侠客。他们平生之愿,便是以自身为剑,斩世间浑浊。但是,他们尚未行尽此道,就被朝廷官员处死了——以‘太平盛世以武犯禁’之名。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官员是因为我父母获知他污藏朝廷灾款、买爵鬻官的证据,才先下手为强。
“行刑时,乡亲们藏起了我。之后数位侠客几经周折,将我送到师父门下,而师父当即收我入门。他和师娘养育我长大,为护我躲避查捕,几经辗转,后来不得不长居深山、远避世事。如今,当年那贪官已被惩处落狱。天道昭然,沉冤得雪,但又如何?死去的人已死,老去的人已老,回不来了。
“家宅生变时我只有十岁。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手中剑再锐、再快,在权贵财势面前,什么也护不住。
“我,不会再走那条路。”
孟莳静静地听我说完,良久,说:“既然你决意走功名一途,又为何要潜心修剑?”
我一愣,闷声道,“自然是因为家师从小棍棒相逼。”
“只是如此?”
“……”
“我看你方才运剑刻碑,如臂使指,人剑气度之合实为少见。以行医者的浅见,心从方能动遂。未能以心纳剑者,不可能至此境界。”
我怔住了。
他望向竹后月光,“我们医门,有‘制身药’和‘炼心药’两重境界。不知你们剑道,是否也有‘传有形之剑’和‘承无形之剑’的两条进路;而少侠循的,又是哪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