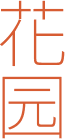作品:第聂伯河上的银月
亲爱的卡佳:
很遗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重新开始通信。很感谢你在第一时间将格奥尔吉教授葬礼的详细安排与具体事件告知我,对此真是不胜感激。基辅的疫情也不容乐观,目前我们这里也暂未恢复往乌克兰的航班,我显然无法参加这个葬礼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这样!本月初格奥尔吉教授还在世时,我曾与他联络,说了这样的话,我说“我以为以人类的文明程度,已经不至于发生这么糟糕的情况了。”教授很平静地回复我:“历史都不止数次瘟疫。”我们互相叮嘱了要多保重,想不到彼日就是永诀之时。
噩耗传来,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一个研究瘟疫大流行历史专题的人,会因为瘟疫的大流行耽误了癌症治疗,因此英年早逝呢?教授去世后这十多日里,我很想联系你们,追问他最后的情况,然而终究胆怯,我过分希望他的最后光景是没有痛苦的,我不要别人告诉我其他的情形。
教授与我共同发起的课题才推进了很少的部分,他交给我的基辅彼切尔洞窟修道院443号伊凡神父墓穴里的墓主人与一名哥萨克游医的鲁塞尼亚语信件,有整整一沓,因为讲课和讲演、采访、出差等等这些俗事的侵扰,我才翻译了其中几页……天啊,那是讲述18世纪初乌克兰疫病大流行时期的信息密码啊!为什么我要耽误时光呢?而现在,这就是大流行的当时,我们位于同样的洪流中,世界会如那时一样转动变化吗?这一次的疾病会像17-18世纪之交的黑死病与霍乱那样毫无先兆出现、又毫无征兆地消失吗?它会像1719年的天花那样,引发医疗的革命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无法参加教授的葬礼,让我感到遗憾和痛苦。有太多的问题我曾经考虑过与他谈论,却又以为时光长远,没有马上谈论。格奥尔吉教授在日,很喜欢向我讲述他们哥萨克人的历史。他常说“哥萨克”是自由人的意思,他说过他的姓氏来由,不是因为血缘,而是因为英雄。哥萨克人的祖先取用英雄大酋长的姓名作为自己和子孙的姓氏,他说过很希望将来再开新的课题,去了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给了他如今这骄傲的姓氏。他说这一切一定是上帝的安排,是基辅圣女巴巴拉遗骸的护佑。可是听着他这些充满激情的言语的我,那时候什么也没有想象,什么也没有说过。回忆起来,一片空白,一片空白。
教授走后,十多天来我一直在担心自己无法独自完成译稿工作,使他所托非人。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无法想象大家在人类任何描绘得出的天堂中与良师益友重逢。我相信,作为宏大宇宙的尘埃,我们终会以某种尘埃的面貌再度碰面的。
希望到时候我能骄傲地告诉他,稿子全都翻译完了,神父的故事是这样那样的。以及,那个哥萨克医生的名字到底叫什么。
想念你。
向叶夫多妮娅、西利维斯特诺维奇、阿里克谢问好。我也很想念他们。最后,向尊敬的亚历山德拉太太致以诚挚的关切,我们都能体会到她的所失,这也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巨大损失。请她节哀。
以上。万望健康。
爱你的孟
1/9/2020 10:29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