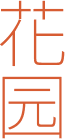作品:都市三题:墓志铭、传奇和挽歌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伦巴德人,他战死在拉文纳。
他的名字叫做德罗图夫特,高大、强壮、白皮肤,金发碧眼,从未修剪的胡子浓密鬈曲。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和家人一起住在易北河畔,因此在他童年模糊的记忆里,有清澈的水流、湛蓝的天空,以及给万物镶上金边的灿烂的阳光。
随着征战和迁徙,部族渐渐向南,走过河流,走过荒原,走过沼泽和灌木丛,走进森林——莽莽无边的森林。长老们说里是日耳曼人的王国,只有日耳曼人能在其中繁衍生息,其他人则会被浓荫与腐叶吞没,尸骨无存。
伦巴德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所以他们在篝火旁讲述的故事里,总是有一个金发的英雄、一群白皮肤的勇士、一条河、一座骄傲而荒淫的城市、一场以屠杀和焚烧结束的战争,城市化为废墟,年轻的女子成为俘虏,老人和孩子在废墟上哭泣……年轻的伦巴德人喜欢这样的故事,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伦巴德人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城市,将之掠夺一空,烧成灰烬。——尽管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从未见过任何一座城市。
所以年轻的伦巴德人便在幻想中,用自己熟悉的材料来建筑城市:参天的巨木、阴险的沼泽、蜿蜒的蔓藤和层层叠叠的青苔……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天空永远浓荫遮蔽,雾气时时泛起,鸟雀和野兽的叫声忽远忽近。茅屋低矮昏暗、没有窗户,猛一看去好像是树下的草堆(所以有人传说日耳曼人都住在树上,像猿猴一样)。只有老人和女人才长时间留在室内,让火炕的浓烟把双眼熏得通红。孩子和男人只在睡觉时才回屋,年轻的男人们甚至睡觉也在外面,除非下雨或下雪的时候。
这些年轻的伦巴德人,他们洁身自好、坚持练武,节日时才喝酒,月圆之夜才和姑娘们睡觉,忠于首领和部族,更忠于他们的神明。虽然首领和长老们已经信奉了基督教阿里派,用十字架上钉过耶稣的铁钉装饰首领的铁王冠,但大多数伦巴德人真正崇拜的还是大神曼努斯和他的三个儿子:雷神、战神和死神,以及大地之母赫莎。
每隔半年,粗糙的木雕神像被放上大车,由白色母牛拉着走过茅屋。人们把各种各样的金属制品放在神像脚下——伦巴德人不会制造金属,所有的东西都是捡来的或抢来的,最多的是钱币,其次是首饰的碎片,还有铠甲上的小零件或箭头。然后女人们会把这些金属缝在粗糙的手织布上,再用来裹住神像。
德罗图夫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喜欢摆弄神像裹布上的金属。他不知道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有着怎样的用途,可是能隐约地感觉到它们属于一个庞大的整体,一个按照他所不能理解的规律运行着的世界。总是让他想起小时候在易北河边度过的那些夜晚,看到的满天星光,让他感动,但又迷茫,几乎带点恐慌。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真正懂得它们,但凭着直觉也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智慧和力量,以及它们在这个世界中重要性。
所以德罗图夫特幻想中的城市没有树木和茅屋,也没有野兽和沼泽,只有金属,无边无尽的金属,以他所不能理解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混乱、荒诞,一如神像裹布上缀着的金属碎片。但他深信其中必定有非同凡响的意义,一如夏夜里的群星。
这样的幻想持续到德罗图夫特十七岁的时候,那一年,他经历了第一场战争,看到了第一座城市——
拉文纳。
拉文纳,城中之城。东西罗马帝国都曾以它为统治意大利的中心。这里有当时最宏伟的陵墓和最华丽的教堂,前者是皇帝赫诺琉斯为他宠爱的妃子珈拉·普拉西蒂亚修建,从罗马各地召集来的工匠,用大理石碎片在大理石墙壁上镶嵌出巧夺天工的壁画,近看繁复绚烂,只有远看才会发现那早夭的美丽女子的笑容从墙壁上隐约凸现,光华流动,见过的人无不将之称为罗马的“宝墙”。后者是圣维达尔教堂,外形朴素,门窗狭小,除了巨大的穹顶,没有任何惹眼的装饰,但走进教堂,就仿佛走进了一幅用镶嵌画连缀而成的华丽画卷,陶片、贝壳、彩色的碎石、金箔和银箔、宝石的薄片与碎屑,将狭小窗户里透进来的微弱光芒染上鲜艳的颜色,无限放大,交织在并不宽广的空间里,宛如梦幻。
除此之外,拉文纳还有大殿、宫室、花园和柱廊组成的皇宫,有着十九层大理石台阶的元老院议事厅和公共学院、可以容纳上万人的环形大赛场和剧院、用于集会和法院公审的大厅、十一座豪华的公共浴池、七十九座私人浴池、二十五条沿街廊柱,以及众多的囤粮谷仓、引水渠、蓄水池、贵族和富人的宅邸,所有这些建筑拥簇向拉文纳广场,广场中心耸立着近二十米的花岗岩石柱,坐落在五米高的白色大理石基座上,圆柱的直径超过三米,顶端是从罗马万神殿请来的阿波罗神像,柱身上却刻满了对诸神的赞颂,全不在意阿波罗是一个多么善妒的神明。——这是真正的罗马,兼容并蓄而漫不经心;这是不朽的拉文纳,伟大的罗马帝国在亚得里亚海边平原上一个最美丽的投影。
然而德罗图夫特最初看到的拉文纳,只是一带蜿蜒的城墙。
战争把他和同伴带出了丛林,带到了拉文纳,他看到了从来没有看见——或者说从来没有仔细看过的东西:他看到了白昼,没有树荫遮挡和雾气缭绕的白昼;似曾相识的湛蓝天空和一泻千里的阳光;阳光下的葡萄园和麦田;修剪整齐的意大利柏树;丢弃在路旁的残破的大理石雕像;还有城墙下胸甲与盾牌的壁垒、标枪的丛林。
伦巴德人没有金属,德罗图夫特和同伴们用的是削尖的木棍或巨大的木棒,他们没有头盔、没有胸甲,盾牌用木头钉成或柳条编成,包裹着皮革。只有首领和大勇士们才佩戴刀剑,给盾牌镶上铁边。他们不懂得阵型、不懂得秩序、不懂得指挥和防守,只听从首领呼啸着喊出的战斗口号,而那口号只是一串野蛮尖锐的音节。尽管如此,自从六百年前第一支罗马军队遇到第一群日耳曼战士,全军覆没以来,日耳曼战士始终是罗马军人的噩梦。
正如伦巴德人成了之后一百年里意大利平原的噩梦。
当德罗图夫特看到拉文纳的城墙时,这个噩梦刚刚开始。交战的双方都不会想到,之后的一百年,伦巴德人横扫意大利平原;之后的两百年,拉文纳陷落,伦巴德人以它为中心建立了伦巴德王国;从此这一片广阔的区域被称为伦巴底,而他们最终成为罗马公民、成为意大利人的一支,被称为伦巴第人。
而在这一刻,德罗图夫特看到的只是拉文纳的城墙。
和他的想象完全不同,城墙看上去并不高,由整齐的石块砌成,有的地方还垂着蔓藤,丛林里常见的蔓藤,甚至开着同样的白色小花,只不过城墙上的花开得更密,在阳光下闪着光,但那不是他曾经梦到过的无边无际的金属的光芒。
还没等他看仔细,战斗就开始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战斗就结束了。拉文纳人逃回城里,留下少量的尸体和更少的伤员。每一次与罗马人交锋,武器落后的伦巴德人都是猛杀猛打、速战速决,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卷入长时间的肉搏,他们简陋的武器在罗马人的长枪和铁甲下便不堪一击。而他们所拥有的,则是罗马人早已失去的速度、灵活、矫健,以及视死如归的凶悍精神。
每一个伦巴德人仍然相信,死在战场上的男人的灵魂,将与曼努斯大神同在,永远地生活在大地之母赫莎四季如春的乐园里。而他们的对手罗马人,却早已不再相信这样的故事。
所以几乎每一场战斗结束,留在战场上的总是伦巴德人,他们翻检死者与伤者,取走武器和盾牌,摘下铠甲和头盔,摸索全身,寻找值得带回的东西。如果伤者醒来,就补上致命的一击。但这一次,就在这样的时候,拉文纳的城门再度打开,罗马人出人意料地又一次发起攻击,这一次他们不止有金属的胸甲和长矛,还有骏马和战车。
年轻的伦巴德人惊慌奔逃,他们中的许多人生平第一次见到战车,伦巴德首领发出尖锐的呼啸,阻止年轻战士的溃逃,一些人被恐惧战胜了责任感,本能地继续奔逃,另一些则停了下来,试图迎战。就在这时,年轻的伦巴德战士德罗图夫特,做了一件不可思议之事。
战车冲出城门时他正跪在一个伤者身边,撕扯他头盔上的纽带,对方苏醒过来,立刻被他拧住脖子,正要将之折断,战车冲到,德罗图夫特完全是本能地护住手下的伤者,翻身滚开,躲过了车轮轴上青铜的尖刺。伤者发出痛楚的呼喊,那是德罗图夫特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如此尖锐凄惨,甚至压住了同时响起的伦巴德首领的呼啸,让他愕然——而这时,德罗图夫特看见,就在自己面前,只有十几步的地方,巨大的城门缓缓关闭,城门上镶嵌的青铜,折射出已经开始倾斜的太阳刺眼的光芒。
于是德罗图夫特做了一件不可思议之事,他抱着惨叫呻吟的拉文纳伤者,站起来,向城门走去。
那一刻阳光格外强烈,为斑驳的城门镀上黄金般的光芒,伤者紫色的披风扫起尘埃,而光芒和尘埃勾勒出蛮族战士抱着伤者走进城门的形象,使得正在关闭的城门为他们停顿了片刻。就这样,伦巴德人德罗图夫特,走进了拉文纳。
拉文纳,城中之城。
第一夜,德罗图夫特站在窗边,俯看拉文纳。
伤者的家人收留了他,两个穿白袍的姑娘为他擦去血污和汗水,给他面包、烤肉和葡萄酒,其中一个甚至愿意和他睡觉。他用手肘轻轻地推开了她,因为他害怕,害怕她描着金色眼线的眼睛,也害怕她似乎一碰就会受伤的娇嫩的肌肤。
那一夜他看到了一些白色的圆屋顶,在月光下柔和的轮廓;看到铺着石板的街道,一个衣着破烂的诗人坐在街角,摆弄着一把竖琴;一只猫沿着屋顶的流水槽溜进一个窗口;白发的老妇人在井边打水,吃力地摇动着辘轳上的手柄;稍远处有车轮滚过石板路,伴随着有气无力的吆喝;再远一些的地方,升腾起黑色的烟雾,人声嘈杂,夹杂着哭泣的声音;更远处,异族的光明之神矗立在高大的石柱上,仿佛正驾着战车向他奔来。
第二天,他迷失在拉文纳。
他走过许多相似的房子、相似的街道,壁画上女子的衣饰与面孔在他眼里都一模一样;每一座拱门上都刻着密密麻麻的古怪的符号;窗户的护栏和楼梯的扶手上都有抓挠和撞击留下的痕迹;弯弯曲曲的水沟以不可理喻的方式匍匐伸展……有一个广场,他许多次走过,又总是会绕回来,但每次那口九眼的喷泉似乎都在不同的方向……孩子们围观他,追着他跑,又在他转身的时候尖叫着逃走,最后变成了一个开心的游戏。有一对小姐妹,逃走时还恋恋不舍地回头偷看他,他对她们笑了笑,小一些的那个便站住,招手让他走近。小姐姐焦急地对她说着什么,生气地跺着脚,但她不理,只是看着他,对他微笑,然后吐出一直含在嘴里的彩色的小石头,送给了他。
小石头握在手里,沾着小女孩的唾液,湿漉漉的;一个牵着狗的老人坐在石墙下,给了他一个面包;穿着白袍的姑娘们提着篮子走过,好奇地打量他,羞红了脸,她们轻声商量了几句,把一只最大的熟透的无花果放进他手里;他还喝了蓄水池里的水,看到水面漾着薄薄的灰尘。
最后他坐在高高的台阶上,看黄昏渐渐降临拉文纳。他终于看到了被传说了千百遍的城市,但对它仍然一无所知。在他那简单的心灵里,迷惑和恐慌是那么强烈,虽然他紧紧握着自己的木棒,牢牢背着柳条编织的盾牌,却还是觉得自己赤身裸体、一无所有,就像刚出生的孩子,甚至像一条狗。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够模糊地意识到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是多么的重要,这里的一个角落、一方碎片,甚至拱门上一行他一无所知的文字,都比日耳曼所有的丛林和沼泽更有意义,比他们崇拜的所有神明还要不同凡响。
第二夜,他睡在白石头的柱廊下,看到月光移动着石柱的投影,仿佛细长的女子的身影。
半夜的时候,有人把他推醒。他看见一双明亮的褐色的眼睛,在伦巴德的丛林里,没有女子有这样明亮的眼睛——她们的眼睛都被茅屋里的烟火熏得红肿浑浊;他看见一张微笑的粉红色的嘴,在伦巴德的丛林里,没有女子有这样娇艳的嘴唇;还有一双纤细的手,走遍整个日耳曼部落也找不到的柔嫩的小手,牵着他,走进了一座庭院。
德罗图夫特彻底变成了一个孩子,一无所知、任人摆布。她在他的耳边说着他听不懂的最温柔的话语,她用银色瓶子里带着花香的水冲洗他的身体和头发,她用洁白的麻布擦拭他的全身,用镶着宝石的象牙梳子梳理他的头发。他回报她以顺从的沉默,孩子般的眼神,茫然而无辜;最后她吻了他,让他占有了自己。
直到这时,德罗图夫特才忽然想起自己的丛林和部族,想起母亲的茅屋、火炕里熏烤的野兔、低低的房梁上挂着成串的野葱和薄荷、木头雕刻的碗、石片磨成的小刀,以及总是和自己睡觉的那个姑娘圆圆的脸和圆圆的眼睛。直到此刻,他才忽然觉得自己已离那一切已经多么遥远,而那遥远的一切,又是多么的熟悉。直到此刻,他才迷迷糊糊地意识到,也许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那熟悉的一切,失去了所有的沼泽和丛林,也失去了年复一年虔诚膜拜的神明。
但是他来不及悲伤,他也不懂得悲伤——太小的孩子还不懂得悲伤,而在拉文纳,他是一个太小的孩子。他只看见镶嵌着贝壳碎片的窗格,在月光下闪着珍珠的光芒;只看见女子柔滑的肌肤上的汗珠,比珍珠更晶莹明亮。
第三天,德罗图夫特走遍了拉文纳。
他看到了那座宏伟的陵墓,像一个平放在地上的巨大的十字架,十二米长,十米宽,墓室内装饰着大理石的“宝墙”;看到了那座华丽的教堂,像两个套在一起的八角形,被巨大的穹顶笼罩,穹顶上描绘着让他窒息的灿烂的天堂;还看到了同样是八角形的正统派洗礼堂,以及克拉斯圣阿伯里奈瑞教堂和圣洛伦索纪念堂。
他还看到了皇宫,看到了巍峨的市政厅、森严的将军府和国库,优雅的私人宅邸和肃穆的图书馆……看到了拉文纳广场的周围大片的公共建筑:浴池、剧院、议事大厅;看到了广场中心高耸的石柱,石柱上刻满了罗马文字……他看到了一个混乱、庞大,但绝非杂乱无章的整体,一个按照他所不理解的规律和意志运行着的完整的世界,一个与他的幻想和梦境绝不相同,但确实是他所幻想过和梦想着的城市。
第三天夜里,他坐在拉文纳的中心,阿波罗神像的石柱下,放声大哭。
他弄丢了他的盾牌和木棒,他的粗布衣裳,他的蒙着粗布、缀着金属碎片的神明,以及他走过的每一条河流、每一片沼泽和每一座丛林。得到了一个他什么也不懂的世界,一个他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走进的世界。
第四天,伦巴德人的呼啸在拉文纳城外响起,德罗图夫特走向整装的罗马军队,用日耳曼语、眼神和手势,乞求一枝长枪。
他们给他穿上罗马人的胸甲、戴上头盔,给他铁的标枪和青铜镶嵌的盾牌。就这样,在第四天结束的时候,德罗图夫特战死在拉文纳城下。
拉文纳人埋葬了他,为他树起墓碑,用他所不懂的文字,写下这样的墓志铭——
他虎背熊腰、虬髯鬈曲,
容貌可怕,却有颗善良的心。
虽然抛弃了他的亲人,
我们仍满怀爱与尊敬,
在拉文纳家乡把他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