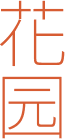作品:都市三题:墓志铭、传奇和挽歌
在大元帝国文人和贵族的宴会上,马可波罗不止一次地想起伦巴德人德罗图夫特的故事:他得到了天启、背叛了族人、皈依了正教,为拉文纳而战,为罗马而死。也许他的族人曾诅咒他、唾弃他,但当他们征服了拉文纳之后,却也像他一样被这座城市所征服,建立起伦巴底王国,最终成为伦巴第人——以艺术和诗歌的成就为整个意大利所称道。
马可波罗不知道如果自己讲述这个故事,是否会有人聆听,并微笑着揣测故事背后的含义——在中国,所有的故事背后都有隐藏的意义。他们也许会猜想这威尼斯人在暗指自己:从遥远的蛮荒之地,跋山涉水而来,沉醉在天朝上国繁华的都城里,并愿意为之献上忠诚、才华和勇气。尽管如此,马可波罗知道,在他们眼里自己仍是一个本不该坐在这里的“异类”,唯一可取之处是会说流利的汉语和蒙语。
或者也许有人会真正听懂他的故事,像他一样冒着大不敬联想起大汗和大汗的蒙古铁骑:他们曾想把中原变成无边无际的牧场,却在他们渴望摧毁成荒野草地的城市里定居,修建华美的宅邸和花园,举行盛宴,饮酒听歌,慢慢老去——但他同样知道,即使是听懂了的人们,也一定会装出全然不懂的神情,漠然地转过脸去,伴随着歌姬的演唱,用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打着拍子。这是中国人的宴会上,客人们最常见的动作和神情。
马可波罗坐在下席的客人中间,觉得难以言喻疲惫和厌倦。这厌倦来自菜肴的美味与油腻,来自歌声的婉转与单调,来自谈话的优雅与拘束,甚至来自空气,大元帝国的都城里特有的空气,既有淋过雨的马粪的味道,又有黄铜雕花的小炉子里燃烧麝香与龙涎的味道。
甚至来自女人,他的宅邸里那两三个侍寝的女人,她们凤目狭长、樱唇小巧、皮肤如象牙,却有着畸形的小脚,即使在做爱的时候也不从脱掉发出酸臭的汗湿的绸缎小鞋。
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曾见过一只这样的绸缎小鞋,崭新、精巧、美得让人不能相信。鞋头塞着沉香末和菊花蕊,散发着略带苦味的芬芳,酒红色的绸缎光滑冰凉,绣着他不认识的繁复的花朵和水草,缀着米粒般细小的碎玉珠子,就连雪白的鞋底都绣着一格格彩色的菱形图案,针脚细密整齐得不可思议。它是如此的小,一只孩子的手就可以握住。马可波罗轻轻握住它,想象这是一只柔嫩的小脚,就像教堂壁画角落里那些用作点缀、垂首低眉的圣洁女子长袍半掩着的小小的脚,于是,这早熟的孩子感觉到了最初的冲动,满脸通红,却久久不肯松手。
而这只绸缎小鞋,只是父亲和叔叔从东方带回的珍玩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他们还带回了镂空雕花的檀香木珠串成的长长的项链;嵌满海螺和贝壳的打磨光滑的圆盘;可以从一个针眼里穿过的如烟如雾的轻纱;绸缎绷成的华丽的风筝;长短粗细不一的笔,笔尖是一簇毛发;洁白如雪的团扇;整张的老虎皮;极细的金丝编织成的羽毛华美的鸟儿,嘴里衔着一串珍珠……这些东西给他的震撼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马可波罗幼小的心灵中,曾以为这世上一切美妙的东西都来自东方,那遥远的太阳升起的帝国,国王被称为 “大汗”。
他那轻浮快活,喜欢吹牛的叔叔告诉他,他曾参加过大汗的盛宴,吃的是盛在银盘子里的孔雀舌头、天鹅眼珠、蜂鸟心脏和老虎的脊髓,酒杯是犀牛的角雕刻而成,酒的颜色晶莹透明,有如水晶,洒着细细的金箔,喝下去时会在喉咙里燃烧,仿佛火焰。用于饮宴的大厅地下铺着一千块玉石方砖,每块都有教堂的窗户那么大,而大汗的宫殿里有一千间这样的大厅,他的都城里有一百座这样的宫殿,而在他的帝国里,有一百座这样的城市。
他的话在小孩子马可波罗心里引起了一种近于狂热的幻想,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幻想渐渐变成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直到他十七岁那一年,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一起,带着教皇给中国大汗的信件和礼物,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路程。
他们从威尼斯出发,进入地中海,而后横渡黑海,来到巴格达。
巴格达的意思是“天赐”,它的繁华迷惑了年轻的马可波罗。阿拔斯王朝伟大的哈里发曼苏尔修建了这座城市,它是一座美丽的圆形的城市,像一朵盛放的玫瑰,底格里斯河就是玫瑰的花茎,还有一片同样美丽的绿叶舒展在花朵下——曼苏尔在底格里斯河西岸修建的离宫,他把它命名为“永恒宫”。据说晚年的曼苏尔就住在永恒宫里,每天从阳台上眺望他的“天赐之城”,等待着它被建成的那一天。
曼苏尔没有等到那一天,甚至在马可波罗他们到来的时候,巴格达城仍然没有最终建成,处处都是工地,但丝毫无损它的美丽。让马可波罗无法想象,当它真正建成的时候,会是何等的宏伟巨大。
他问叔叔,大汗的都城是否比巴格达更繁华美丽。叔叔回答是的,他说如果巴格达是“天赐之城”,那么大汗的都城就是天堂本身。
之后她们离开了巴格达,来到霍尔木兹港口,等待前往中国的货船。等了两个月没有消息,便决定改走陆路,从霍尔木兹向东,走过危险的伊朗沙漠,走过寒冷的帕米尔高原,走过喀什、走过和田,继续向东,穿过荒无人烟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经过敦煌古城,最终看到了长城。
这时,距离他们离开威尼斯,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年。
马可波罗始终记得自己看到长城的那一天,漫天黄沙,远远看去,长城低矮残破,无精打采地蜿蜒在荒漠中,他甚至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一跨便能越过。也许是走过了太长的路,也许是做过了太久的梦,眼前那黄土夯成四四方方的小城堡——玉门关,几乎像是一种嘲笑。
就是从那一刻起,幻灭的惆怅在马可波罗心底缓缓升起,从此挥之不去。
即使日后,他在江南最美丽的城市最优雅的园林中品茶,在中原最古老的城市最恢宏的庙宇里瞻仰佛像,或是在最富庶的城市最热闹的市集间闲逛,在最奢靡的城市最昂贵的酒楼上喝酒……即使他走遍大元帝国,看到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塔楼、最坚固的石桥、最大的无边无际的盐田、最长的人工开凿的运河、最广阔的绵延千里的田野、最漫长的年年加固的河堤……在马可波罗内心深处,仍然时时被无以名状的空虚之感所笼罩。
甚至直到他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大汗,并成为大汗的一名官员,穿起了圆领窄袖、左右开衩的官服,围上玉片连缀而成的腰带,学会了朝堂上、官府中和日常生活里各式各样的礼节,学会了用白底蓝花的瓷盖碗品尝不同时令的茶叶,看更漏和日晷标示的时辰,用毛笔写出歪歪扭扭的汉字,品评歌姬弹奏琵琶的指法,感受中国诗句的优美与别扭……他甚至相信所有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无论他们来自阿拉伯、罗马还是西班牙,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不会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个国度,比他走得更远、看得更多。但他仍然觉得空虚。
这是一种再深的了解和再强烈的感受也无法填满的空虚,就像他曾看过大汗那张著名的地图,由十九张完整的牛皮连缀而成,用令人敬畏的黄褐色线条勾勒出古往今来最庞大的帝国,帝国里所有的山川、河流和城市。却让他联想起第一次看到的长城和玉门关,那漫天黄沙中低矮残破、无精打采的土墙。并恍然觉得,这曾被他、被所有人无限赞美无比憧憬的天朝帝国,其实不过是一个土黄色的矮墙围起来的庞大的废墟。他看到的只是无数注定要坍塌的城墙和塔楼,而废墟里幸存的雕花的柱子和栏杆,也会被白蚁慢慢地啮噬成粉末。
是的,废墟。离开威尼斯的时候,马可波罗十七岁,心里藏着一个完整的天朝都城;而现在,他已经在中国度过了十七年,同样漫长的时间,足以将这座城市化为废墟。
如果他的天朝都城最终化为了废墟,那么他漫长的旅途是为了什么呢?比这更漫长的憧憬和幻想又是为了什么呢?而比两者加起来还要漫长的在中国的生活和游历,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之后,有时候他会像一个中国人一样感受和思考。他回顾那座他梦想中的都城,会意识到梦想并非来自自己的心灵和憧憬,更多的是来自偶然。如果那一年他不是恰好已经满了十七岁,如果他不是出生在父亲和叔叔的家庭,如果他不是威尼斯人,如果他不曾偶然地握住那只绸缎小鞋……那么这座都城也许根本不会存在,也就不会渐渐空虚,直至坍塌;而既然是由许多个偶然堆砌而成的幻象,那么它是完整还是破碎、长存还是坍塌,又有什么意义。
但更多的时候,马可波罗仍然是一个局外人,大元帝国和天朝都城的局外人。他看到连年的丰收让粮仓满溢,看到官道和运河上的交通日益繁忙,看到来自四面八方人们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王国派来使节,愿意年年进贡马匹、美女、药材和珠宝,以换取帝国军队的保护;也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越来越复杂、森严和残酷,无边的田野里百姓仍然贫弱怨恨;大汗和他的贵族建起了过多的宫殿和宅邸,以至于上涨的河水带来再多的木材、深山里开采出再多的石料与金属,仍然不够使用;而繁华带来的不再只是快乐,更多的是臃肿、紧张和沉闷……这使他渐渐明白了他那梦想中的都城并非因空虚而坍塌,而是因为他一点点地将现实的重负加在它之上。
与此同时,他还发现自己开始在梦境和幻想中,去往另一座城市。
那是一座真正的梦幻之城,没有任何现实的重负:像水流一样通透,像拱桥一样玲珑,像尖头小艇一样轻盈,像中国特有的水墨画一样洗净铅华,只余玲珑剔透的骨架,清晰素净的剪影。那里有一百一十八个小小的岛屿、一百一十七条细细的运河、三百五十座短短的小桥。人们在水底一根木头挨一根木头地打下地基,铺上木板,再在木板上盖起房子。为了建造这座城市,北方的森林消失了,所有的树木都沉进了这座南国水城的水底,所以曾有人说,这座城市上面是石头、下面是森林。水流交织其间,小艇在水上穿梭,整座城市就像花边一样通透,像叶脉一样清晰,像风筝一样轻盈,就连镶嵌在城市建筑上的累累的黄金、白银和宝石,在倒影中也变得飘忽流动,仿佛液体……而那座城市的名字,就叫做威尼斯。
不知为什么,在中国,马可波罗从不曾对人讲起过威尼斯,或许是觉得无从说起。也许威尼斯曾是意大利最富庶和强大的城邦,也许它的奢靡和堕落曾为教会所憎恨不齿,但十七年前离开的那个孩子并不记得这些。那个孩子记得的只是小船穿过桥洞时湿漉漉的阴影、桥头的香橼树开满的白花、船夫的歌声从窗下传来、狂欢之后漂浮在水面上的华丽面具、一个戴着黑色面纱的少女从桥上走过……有时候,闭上眼睛,他仿佛还能感觉到贡多拉轻微的摇晃,还能听到远远的修道院里缥缈的合唱,但所有这些都只是碎片,随着时光的流水渐渐飘远,闪烁着越来越美丽,却也越来越微弱的小小光芒。而在梦中,他仿佛又变成了那个十七岁的少年,幻想和憧憬变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想要朝着那微弱的小小的光芒,走回去。
一如十七年前,那个少年朝着灿烂的天朝都城的光芒走来。
从这样的梦中醒来,马可波罗知道,已经到了他应该离开的时候。
他曾经听过一个古老的中国哲人的故事,哲人在梦中变成一只蝴蝶,翩翩飞去,醒来后不知是自己在梦中化为蝴蝶,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一个老哲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马可波罗觉得它精巧、荒诞而无聊,就像许多中国古老的故事一样。然而现在,他觉得这个故事似乎就是为他而写,他同样不知道自己是为着那座梦想中的都城而离开了威尼斯,还是为了回到威尼斯而来到这里。他只知道,即使他回去,十七年前他离开时的那个威尼斯,他已经回不去了。
正如十七年前梦想着的那个天朝都城,他从来不曾到达。
也许这世上所有的离开和所有的到达都是如此。尽管这样,人们仍然要启程。
就这样,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离开了大元帝国的都城,踏上了回乡之旅。在离开前的最后一夜,他做了一个奇异的梦。
他梦见了大汗——他从来没有机会单独觐见,更没有机会与之交谈大汗。他梦见大汗站在城墙上,身后是宫殿金黄色屋顶的海洋,面前是宽广整齐、横平竖直的都城,大汗对他说:“爱卿,去为朕修建一座都城。”
“朕的帝国曾如骏马奔腾般扩张,马鞭所指之处,皆是帝国的领土。”大汗这样说,“然而有一天,朕厌倦了这样的帝国,它已经向外生长得太远,该是向内生长的时候了。于是一座座城池有如熟透的石榴,在帝国参天大树的枝条上爆裂开来。但枝条因此被压弯,大树也不能再恢复直指云霄的生长之势。
“而到这时,朕已然知晓,所有的城池都将化为废墟,朕的帝国也是如此。所以爱卿,去为朕修建一座都城:一座既不在东方也不在西方,同时既在东方也在西方的都城,一座不会因为战争化成灰烬,也不会被马蹄踏为废墟的都城,一座不会在繁华中腐烂也不会在荒芜中凋零的都城,一座时间的流逝和朝代的更替也无能为力的都城,一座无人可以到达而又无人不知的都城——”大汗的声音突兀地结束于一个不可理喻的句子,马可波罗忘记了朝堂上的礼节,惊愕地抬起头,却发现眼前已经是一片废墟。
在梦中,马可波罗做出了不可思议之事,他像中国古代书籍中那些忠诚而悲哀的臣子,跪倒在尘埃与瓦砾中,用额头撞击百孔千疮的地面,用字正腔圆的大都方言说出了他从来没有机会说出的三个字——“臣遵旨”。
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他甚至觉得嗓子发紧,泪水几乎涌上眼眶,就好像转眼间化为废墟的是他的故国,而尘埃与瓦砾下掩埋着的,是他的都城。
从这样的梦中醒来,马可波罗那已经属于中国人的一部分,立刻明白这是一个大凶之兆:它预示着帝国的毁灭和都城的坍塌,预示着中国将再一次陷入战火与纷争,预示着他所熟悉的一切:庭院和花木、雕栏和窗格、繁华的都市和热闹的市集、奢靡的宴会和单调优美的琵琶演奏、巷子口每到春天就会繁花满枝的桃树、桃树下懒洋洋晒太阳的老乞丐、空气中弥漫着的花香和马粪味道、马车织锦的窗帘下偶尔露出的洁白如玉的手……所有这些,在他离开之后,都注定要化为乌有。而他始终属于局外人的那一部分,则不无惆怅但也不无释然地意识到:正如无论走得多远,他最终还是要回到威尼斯;同样,无论走得多远,他也永远不可能真正离开中国。
千年前的老哲人,不知是自己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自己;而从威尼斯来到中国,又从将中国回到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则不知道自己是因为到来而失去,还是将因为离开和失去而得到。
是不是只有离开才能将现实的重负从他梦想的都城中剥离,拂去太长的时间太久的梦想积累的厚厚的尘埃。是不是只有踏上漫长而艰辛的路程,知道余生里再也不可能回去,已经有沙漠和荒原、雪山和大海再一次横亘在两个世界之间,他才能够再一次完整地拥有那座梦想中的都城:一百座黄金屋顶的宫殿、一千间玉石砌成的大厅、三千个凤目狭长、樱唇小巧的女子,穿着绸缎小鞋的脚踩过厚厚的落花……所有你能够想象和想象不到的最珍奇的东西莫不云集于此:刻着狰狞兽面的青铜大鼎;嵌满螺钿与贝壳的紫檀屏风;绣满蔓藤与水草的丝绸和锦缎;竹子的薄片穿成的长卷,上面用古老文字书写着神秘而充满智慧的故事;十九张牛皮连缀成的巨大的地图、用令人敬畏的黄褐色线条勾勒出古往今来最庞大的帝国,帝国里所有的山川、河流和城市……就这样,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他三十八岁的那一年,离开了大元帝国的都城,踏上了回乡的路。
离开的时候,他也许频频回望,也许没有;也许已经开始构思他那部日后传遍欧洲、引起了无数争议的游记,也许还不曾。
也许他已经知道,必定会有人循着他的故事去寻找那座天朝都城,但同时他也知道,没有人能够找到:它既不在东方也不在西方,同时既在东方也在西方;它不会因为战争而化为灰烬,也不会被马蹄踏为废墟;不会在繁华中腐烂,也不会在荒芜中凋零;时间的流逝和朝代的更替都对它无能为力……那座都城,没有人可以到达,然而无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