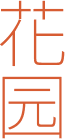作品:《阅微》今译
[好学]
作者纪昀的表弟安中宽(这个名字取得好)说过这么一件事儿:曾有人行走林间,遇到两个人,貌似书生,一边走还一边吟哦不止。其中一个不小心掉了一个笔记本,被这人捡到,随便翻翻,实在是一笔烂字,只能勉强辨认,记的也是乱七八糟,什么药方、符咒、春联、顺口溜、歇后语,全混在一起,还夹杂着诗词名句。
这人正看得一头雾水,失主已经飞奔而来,一把抢回,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因为身形速度太快,所以当事人严重怀疑自己遇到的是两个爱好文艺的狐妖。(为什么不会是两个爱好文艺的武林中人呢?)
同样因为他们动作太快,笔记本里掉下一张纸条也没有注意。当事人迷惘地捡起纸条,只见上面写的是:《诗经》里“於”字都念作“乌”,《易经》里“無”字左边少一个点。(典型的文艺青年小抄么,呵呵……)
作者也认为这是不通文墨的文艺爱好者做的笔记,但他对这种行为持赞赏态度,他说:“能够在业余时间用心文艺学习,不是比吃喝嫖赌要强么。如果我们这些读书人对这样的人才能够鼓励一下,一定能涌现不少自学成才的典型。可惜的是大多数读书人对此都采取嘲笑态度,这是有违圣贤忠厚之道,扼杀好苗子的行为。我见过太多做学问的人,故意把学问的门槛设得很高,让有心向学的人望而生畏,而在我看来,这恰恰说明他们自己是些心肠冷漠的沽名钓誉之徒。”(这话有道理,特别是最后“心肠冷漠的沽名钓誉之徒”的定论,太痛快了。)
[贞狐]
有一个穷小子叫张四喜,家中实在太穷,于是出门打工。到山中一户人家当园丁,表现优秀,得到主人夫妇的赞赏和喜爱,便把小女儿许配给了他。
夫妻感情很不错,张生活得心满意足。就这么过了几年,主人夫妇到塞外看望长女去了,张就领着媳妇到别处安了家。
天长日久,张渐渐发现自己娶的是个狐女,开始觉得很不爽,想要摆脱她,又不敢明说。于是某天趁她一人独处的时候,悄悄射了她一箭(什么什么人嘛)。却没射中要害,狐女拔出箭,纵身跃至张面前,怒斥他负心:“我是狐妖没错!但又不是那种和你偷情苟合,吸你精气的狐狸精!我们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行过拜天地的大礼,我就是你名正言顺的老婆!你怎么能这样对我,真是负心到了极点!”说着哭了起来,握住张的手,叹息道:“尽管你这样无情,我却不能不守为人妻子的道义,既为夫妇,我就不能把你当仇人看待。而你这样讨厌我,我也不能再和你生活在一起了。以后你好自为之吧。”说着就消失了。
张只得两手空空地回了老家,过了几年就贫病交加而死。家里穷得没有棺材入殓,尸体就停在床上。一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女子进门,抚尸大哭,原来她就是那个狐女。她哭过之后,正式拜见张的父母,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然后说:“我始终还是您家的媳妇,一直没有出嫁,所以今天不请自来。”又拿出银两来商量安葬事宜。
张的母亲觉得这媳妇真不错,又想到去世的儿子,不觉连哭带骂的数落儿子不像话。旁边几个邻居家的大妈也为狐女不平,跟着张妈妈数落。狐女怒目而视,说:“做父母的数落儿子没有关系,你们怎么能当着我这做老婆的面,说我老公的不是!”说完就离开了。
此后狐女再也没有来过张家(希望是恢复自由之身后又幸福地出嫁了),但张家二老总是能够在家里发现一些钱粮,晚景才不至于太凄凉,大家都知道,这是那狐女在接济他们。
[刺血诗]
作者纪昀校勘《四库全书》的时候,在《永乐大典》里发现一首诗,题目是《李芳树刺血诗》,没有朝代题跋,因此不知作者是谁,写诗的前因后果。但诗写的很美,缠绵悱恻,怨而不怒。所以作者抄录下来,一直带在身边。
诗句如下——
去去复去去,凄恻门前树。
行行重行行,辗转犹含情。
含情一回首,见我窗前柳。
柳北是高楼,珠帘半上钩。
昨为楼上女,帘下调鹦鹉。
今为墙外人,红泪沾罗巾。
墙外与楼上,相去无十丈。
云何咫尺间,如隔千重山?
悲哉两决绝,从此终天别。
别鹤空徘徊,谁念鸣声哀。
徘徊日欲绝,决意投身返。
手裂湘裙裾,泣寄稿砧书。
可怜帛一尺,字字血痕赤。
一字一酸吟,旧爱牵人心。
君如收覆水,妾罪甘鞭捶。
不然死君前,终胜生弃捐。
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
傥(即“倘”)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
(看到这样的诗句,总是要叹息,对方如果变了心,别说写首“刺血诗”,写《一千零一夜》都不顶啊。)
[明玕]
作者纪昀有一个侍妾,姓沈,作者给她取名“明玕”。她虽然出身小户人家,但自幼容貌气质出众,有大家风范。因此对自己的归宿有独到的想法,曾悄悄对姐姐说:“我不愿意嫁入蓬门,辛苦一生,富贵人家又不会与我们这样的人家联姻。想来想去,最好的归宿竟是嫁到富贵人家作妾。”姐姐把她的想法告诉了父母,父母也就遂了她的心愿,将她嫁给作者为妾。
沈氏性情很好,聪明温柔(这四个字真正难得),生平未曾得罪过一个人(宝钗之流也)。刚嫁进来的时候,拜见作者的正室马夫人(纪昀的正室,名月芳),马夫人对她说:“听说你自愿为妾,但你可知,妾不易为啊。”(不是省油的灯。)她恭敬地行礼回答:“只因人皆不愿为妾,故妾不易为;我真心甘愿为妾的,妾有何难为。”马夫人听了这话,对她另眼相待,两人一直处得很好。
沈氏嫁进来的时候,只是识字,并不知书,后来陪作者检点书籍,耳濡目染,竟能够写些浅白的诗句。曾对作者说:“女子当死在四十岁之前,还能赚得些同情悼念,四十岁以后青衣白发、老态龙钟的样子,我可不愿被你看到。”谁料一语成谶,她去世那年,正三十岁。
去世前,她把自己的小像留给女儿,并赋诗一首:“三十年来梦一场,遗容付女手收藏。他时话我生平事,认取姑苏沈五娘。”
沈氏去世后,作者回忆她病重的时候,自己在圆明园值班,住在海淀的别墅里。有一天晚上,恍惚间两次梦见沈来到身旁,以为是自己挂念所致。后来才知道,那晚她晕绝两次,醒来后对旁人说:“方才去了海淀别墅,见到老爷,忽听得一声巨响,如惊雷一般,便醒了过来。”作者因而记起梦见的那夜,确实有一声巨响,是墙上挂瓶的绳子断了,掉了下来,由此可知,那夜梦中所见,竟是沈氏的生魂。
作者有感而发,在她的遗像上题诗——
其一:几分相似几分非,可是香魂月下归?春梦无痕时一瞥,最关情处在依稀。
其二:到死春蚕尚可丝,离魂倩女不须疑。一声惊破梨花梦,恰记铜瓶坠地时。
[殉情]
作者纪昀曾听到这么一件事儿:雍正年间,某人的一个侍妾坠楼身亡。当时主人家很忌讳说这件事,时间久了人们才知道真相。
原来这侍妾是山东人,十四五岁的时候嫁入一个贫苦人家,但小夫妻感情很好,一直形影不离。不久遇到饥荒,家人断了生计,公婆就把她卖给了人贩子。被卖的前一夜,夫妻俩相拥痛哭整宿,彼此啮臂为盟,发誓一定要想法再相见。女孩子被人贩子带走后,她的丈夫也离开家,一路乞讨跟随着她们,直到京城。偶尔两人能够隔着车窗或轿帘见上一面,但只能相对落泪。只有一次,两人终于有机会说上话了,彼此约定一定要活下去,世事变迁,也许还有机会再续前缘。
后来女孩子被某人买作侍妾,男孩子就投身给这家的一个清客作仆人,也算是守在一起,只是内外隔绝,无法通音信,女孩子一直不知道前夫和自己在一家。直到有一天,男孩子病死了,家中下人偶尔在女孩子面前说起,女孩子起了疑心,追问年貌特征,才知道那是自己的前夫。
当时她正和众侍妾陪着主人坐在楼上,呆了很久,忽然站起身来,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长叹几声,坠楼而死。
这也算是一个贞烈的殉情女子,只可惜当时人们议论这女子不死在人贩子手里,不死在被卖为妾之前,直到另嫁他人,白璧有瑕之后,才因为前夫的死讯而自杀,还是死得太晚了。(真真气死我了!说这种话的大人君子,死给我看看先!)主人也因此避讳这件事,使她的事迹没能流传。
而作者认为,这件事根本不应该避讳。但凡女子殉夫,无非两种情况,一为节,一为情。为节的宁死不辱,捍卫夫妻道义,力量来自礼教的熏陶;为情的则可能忍辱偷生,无非是希望破镜重圆,直到彻底绝望的时候才会以死相殉,这力量来自内心的情感。而这坠楼的侍妾其实早就有殉情的念头,只是因为和前夫感情太好,不忍割舍。在她的心中,众人所谓的“当死不死”并不算是负了夫妻情谊,不能一起守约活下去,才是辜负彼此。所以我们只要为她的遭遇而难过,为她的心志而感动就可以了。而那些大人君子们,一定要用礼教大义,来苛责这一对没有读过书的小儿女,未免太忍心了。(说得好!)
[绝情]
作者纪昀曾和朋友们聚会,聊天聊到狐妖(看来古往今来,大家FB的时候话题都很无聊啊),一个朋友说了这么一件事儿:一个姓纪的书生,曾经傍晚遇到一个女子独行,当时道路泥泞,女子很是困窘,态度柔婉地拜托纪生搀扶自己一下。纪生估摸她是狐妖,但也不怎么害怕,反而很好奇,想和她亲热一下,好知道和狐妖亲热究竟是什么感觉。(爆,什么动机?)
所以纪生对她说:“我知道你的底细,你也不必再费心骗我了。但你生得这样好,我怎能不动心。这里人多,咱就别拉拉扯扯了,免得生出事端。晚上你到我的书斋来,咱们再说。”女子便一笑,自个儿走了。
半夜女子果然来了,与纪生一连缠绵了几个晚上。纪生觉得自己开始把握不定了,就对狐妖MM说分手。MM不愿意,和他吵闹,他正色说:“别来这套。男女之事,主动权在男方(管他有理无理,听到这话先扇他几个耳光再说:),男求女不成,还可以用强(再扇),女求男而男方不愿意,那一定是心如铁石,就算你用强也没辙。(NND,真对他用强试试!——我错了,这种人有什么好用强的。)何况你来就我,是为了取我的精气(大帽子压下来了),并非对我有情,所以我不算负心。而你想必阅人多矣,谈不到节操,我也不算是坏了你的名节。‘始乱终弃’确实是君子不齿的行为,但这是说人间的女子,不是说你们,所以你不必做出恋恋不舍的样子,对我是没有用的。”
狐女闻言,不能说一个字反驳(切~是懒得和这种人费口舌吧),转身就走了。
[责人]
某地有河,平时水流清浅,可以涉水而过,但到了雨季则会涨水,常有不知底细的外乡人在雨季过河时出事。
某年曾有一个讨饭的女子,在雨季过河,她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扶着年迈有病的婆婆。到了河中心,水流忽然变急,婆婆摔了一跤,眼看要被卷进激流。情急之下,女子把怀中的孩子扔进水里,双手拉住婆婆,孩子转眼就被水流冲走了。
上岸后,婆婆痛哭怒骂:“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子,死了有什么关系!咱家几代单传,指着这孩子延续香火,你居然把他扔到水里!让咱家断子绝孙的罪人就是你啊!”女子只是长跪痛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婆婆一步不肯再多走,在河岸上哭了两天之后,便去世了。女子呆坐了几天,形容枯槁,最终也死了。
人们议论这一家人的不幸遭遇,忍不住要讨论一下女子抛儿救婆婆的举动到底对不对。有人说,婆婆当然比儿子重要,但祖宗又比婆婆重要。如果这女子的丈夫还在人世,或者丈夫还有兄弟,那么她的行为无可厚非。但从她婆婆的话来看,她们家竟是两代寡妇,只这一个孤儿,那么婆婆的指责就有道理,而女子的举动则太欠考虑了。
作者的父亲纪容舒老先生听到这种论调,非常愤怒(我听了也怒),他说:“道学先生责备起旁人来,真是混帐没有止境。
“当时激流汹涌、人命关天、千钧一发。哪里有时间给人做这么周密的思考分析?势难两全的时候,女子放弃儿子,救了婆婆,完全是凭着她将长辈和孝道看得最重的本能行事。假使她当时放弃了婆婆,选择了儿子,她难道不会为之后悔一辈子吗?那些道学家想必也会用另一套说辞来责备她吧。
“况且她的儿子还是一个婴儿,将来养不养得活还未可知,假如她放弃了婆婆,而将来孩子又夭折了,那时又该是什么情形?!在那种情况下,这女子的举动,已经比寻常人了不起太多了。只可怜她的婆婆一时想不开去世了,她又随之以身相殉,真是太可怜太让人难过了。
“面对这样的人间惨剧,道学先生们还沾沾自得地摇动三寸不烂之舌,以为自己把人情世故孝道精神揣摩得很透彻,使贞洁孝顺的可怜女子死而蒙恨,不得安宁,这是什么样的心肠啊!
“孙复(北宋儒家学者、经学家,与胡瑗、石介一起被后人合称为“宋初三先生”)写《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二百四十年的历史人物没有一个得到了他一句话的赞可;胡致堂(宋代学者)著《读史管见》,除了三皇五帝,历史上就没一个好人了。他们都很有道理,和那些道学先生们一样,但这样的道理论调,我实在不爱听!”
(感叹:纪老先生啊,您真是英明伟大!宽厚仁慈!原谅晚辈无礼,之前的译文中对您曾有嘲弄,晚辈该死,晚辈给您赔礼了……如果像您这样的人更多一些,这个世界都会更好一些。)
[炼心]
作者纪昀的朋友郭石洲曾经说过这么一件事儿:他有一个姓朱的朋友,和一个狐妖关系很好。有一天,他们一起喝酒,狐妖大醉,在他家的花园里睡了一觉。醒来后,发现朱守在自己身旁,朱很好奇地问:“我看笔记小说里写到你们的时候,都说你们醉了就会恢复原形。我怕您也出这样的状况,所以给您盖了件衣裳,又一直守在您身旁,怕给别人看见,对您不利。可是您竟然一直没有变形(怎么好像有点失望的口气),这是为什么啊?”
狐妖回答:“这和道行的深浅有关,道行浅的只能幻化外形,所以一旦入睡、醉酒或惊慌失措,失去定力,就会打回原形。而道行深的已经从内到外、发自内心地成为了人,就不会变化了。”
朱这才知道自己交到了一个了不起的狐妖,于是想向他学道。狐妖摇头道:“你做不到啊。”
朱不肯信,狐妖解释给他听:“但凡修道,靠的是‘气’,人的‘气’纯,动物的‘气’杂,所以修道人比动物容易上手;而成道靠的却是‘心’,人的‘心’杂,而动物的‘心’纯,所以动物反而比人容易成道。(插话:想到古人曾说,学道之事,聪明者易入门而难以坚持,愚钝者能坚持而难以入门,哪里去找又聪明又愚钝的人来成就大道啊。其实不止学道,世上一切事都是这样。)实际上,要修炼外形应该先炼‘气’,而要炼‘气’则应该先炼‘心’,只要‘心’定下来了,则气定神闲,随意幻化而不会打回原形,一旦‘心’涣散了,一切幻化伪装就都不能持久。而要炼心修道,必须做到与世隔绝,只与天地宇宙沟通,而将人世间的一切事摒弃在自己的世界外,几百年如一日,心如止水,您觉得您能做到么?”
朱想想自己确实不能,便一笑了之。
作者由此想到另一则“炼心”的故事,他的一个同僚和一个旦角相好,曾问这旦角:“你是怎么能够在演艺圈出类拔萃的啊?”
旦角回答:“我们是以男子之身扮演女子,因此不止外形要变成女子的模样,连心也要变成女子的心窍,然后就能够展现种种柔情媚态,让人消魂。如果心底还存着一丝男儿的意识,那么就必定有那么一丝神情气质不像女子,哪儿能和那些真正的女子们争宠呢?到扮演具体角色的时候,如果演的是贞洁女子,就先要让自己的心端正贤淑起来,那么即使玩笑戏噱的时候仍然不流于放荡;如果演的是荡妇,就要让自己的心先淫荡起来,那么即使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观众也知道那是一个荡妇;演贵族女子要先让自己的心尊贵高傲,那么即使穿戴朴素贫寒也掩盖不了贵族气质;演卑贱女子就先要把心气放低,那么即使穿戴华丽还是看得出出身低贱;演贤惠女子要先让自己的心温顺柔婉起来,那么即使发怒的时候也不会让人觉得泼辣;演泼辣女子则要先存着满心戾气,那么即使在一言不发的时候仍让人觉得乖张难缠……凡此种种,以至喜怒哀乐、爱恨嗔痴,无不应该为角色设身处地地着想。只有你不觉得自己在做戏,把戏里的种种当了真,观众才会觉得那不是演戏,是真的。其他人和我演一样的曲目,一样的角色,但他们往往只能像女人那样行事,而不能像女人那样想事;只能模仿种种女儿家的姿态,而没有真正女儿家的心肠。所以我是演得最好的一个。”(无话可说,服了,表演大师啊……)
作者的朋友李玉典听说了这番高论,感慨道:“说的虽然是不入流的事,道理却是真正的大道理。天底下任何事,都必须用心才能做好,从没有听说过有谁专心一件事而做不好的。专心于一项技能,就能成专家,专心于一件工作,就能圆满完成,小到一门手艺,大到治国平天下,靠的都是用心啊。”
[拒狐]
有一个书生,雨夜独坐,忽然有一个美女闯了进来,说自己是邻居家的女孩子,对书生仰慕已久,所以今夜不避羞耻,冒雨前来自荐枕席。
书生说:“这么大的雨,你身上没有一点打湿的地方,用膝盖想也知道你不是人间女子,你当我白痴啊?!”
女子被他的粗暴态度弄愣了,半天才承认自己是狐妖。“但是,我爱慕您的心一点不改,还是很真很纯的哟!”狐妖MM强调说。
“那又是为什么呢?”书生的态度还是很生硬。
狐妖毫不气馁,含情脉脉地说:“因为我们前世有缘啊。”
书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气势反问:“前世有缘?谁说的?哪儿记着?该谁管?谁告诉你的?为什么不告诉我?发生在什么朝代哪一年几月几日几时几分几秒?那时侯你是什么人?我又是什么人?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结缘?你说!你说!说说说!”
狐妖完全彻底懵了,半天才说:“你几千几百夜不这么独坐,偏偏今夜坐了一会儿就遇见了我;我见过几千几百的少年郎,毫不动心,偏偏看见您就芳心大动,这不是前世有缘,又是什么呢?”
书生说:“您见了我芳心大动,我可是一点儿也不心动。如果心动就是前世有缘,那我毫不心动,就说明我们没有前缘。您呀,也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哪儿来回哪儿去,爱谁是谁,恕不远送。”
狐妖MM顿时石化,不知该怎么办。这时听到窗外有人说:“小丫头不懂事,跟这样的呆子浪费什么时间。”于是MM一挥袖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嗜棋]
围棋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有不少人沉迷此道,荒废了正事,也闹了不少笑话。
当年有一个道士,很喜欢下棋,人们称呼他为“棋道士”,时间一长,把他本来的法号都忘记了。作者纪昀有一个堂兄,某次去拜访棋道士,见他的屋子里摆着一局棋,下了一半,而人不知去向,估计他出去了,就等了一会儿。忽然听见窗下有人喘气的声音,一看,是“棋道士”和他的一个棋友,两人的四只手揪在一起,原来是抢一枚棋子,从屋里打到屋外,两人都死不松手,最后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看到的人无不绝倒。
又曾有一年科考,两个考生在考场里用号板(科举考试时供考生答卷兼睡觉用的木板)画了张棋盘,把石头砸碎了当白子,捡些炭渣当黑子,下了三天三夜的棋,最后双双交了白卷。(这太强了!)
作者于是发表感慨说,下棋这个东西,虽然是个高雅爱好,太沉迷了也不好,尤其不应该被胜负左右自己的喜怒情绪。
苏轼曾说下棋“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王安石也曾有“战罢两奁收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的诗句。然而这两位也只是说得漂亮,考察他们的生平,胜负心也很激烈,但即使如此,他们的说法也值得我们深思。
曾经有人画了一幅《八仙对弈图》,请作者题诗,画的是韩湘子和何仙姑下棋,其他五个神仙在一旁观看,只有铁拐李枕着葫芦呼呼大睡。
作者便题诗二首——
其一:十八年来阅宦途,此心早似水中凫。如何才踏清明路,又看仙人对弈图。(这里的“清明路”,指的应该是清净明澈的心路。)
其二: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那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
[蛇妖]
曾有人在深山消夏,借住农家小院。某日黄昏,他打开门窗纳凉,看见院墙上露出一张美女的脸,五官清秀姣好,对他微笑。他估摸着是邻居家的女儿伏在墙上看自己,不由得大动心特动心。这时,忽然听到院子外面众人惊呼,嚷嚷有一条大蛇盘踞在墙外的树上,蛇头搁在墙上。某人大惊失色,赶紧关上门窗,蛇妖这才缓缓离开。(这样蛮干,果然蛇妖比狐妖要强悍得多啊。)
[质朴]
有一个乡下人,家里很穷,靠给人打小工过日子,收入还要用来接济守寡的嫂子。正是靠了他的接济,寡嫂得以终身守节。
有一天,这个人半夜还在烛光下拈麻线,忽然有一个小人从窗纸的破洞里探进头来,铜钱大小的小脑袋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某人一时好奇,一把把它抓在手里,一看,原来是一个玉石雕刻的小孩子,大概四寸长,雕刻精细,栩栩如生,上面还有点点斑痕,仿佛在土里埋了很多年。
乡下地方偏僻,没有人买这稀罕玩意儿。这人就把它当了四千文钱。当铺老板把这小玉人儿锁在柜子里,很是珍视,但有一天它还是不翼而飞。当铺老板很担心这人来赎的时候怎么交代,很长时间惶恐不已。这人听说之后,一笑置之:“本来就是来历不明的玩意儿,我也是碰巧抓到的。怎么能拿来妄取不义之财呢。”于是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当铺老板说了一遍,并且把当票还给了他。
当铺老板很感动,觉得这真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于是常常找他给打些零工,报酬也给的很大方,还时时周济他。天长日久,这人的生活渐渐上了轨道,最后竟成了小康人家。
[狭隘]
有人在西湖边扶乩(这项娱乐活动的受欢迎程度还真不一般啊),降坛的仙人写了一首即景诗——
我游天目还,跨鹤看龙井。
夕阳没半轮,斜照孤飞影。
飘然一片云,掠过千峰顶。
还没写完,有一个旁观的人就悄声嘀咕:“‘夕阳半没’,那叫返照,就是司马相如所说的‘凌倒景’(司马相如几时说过“凌倒景”已不可考,但李白经司马相如琴台时所写的诗中倒是有“含笑凌倒景”的句子),怎么是‘斜照’呢?”
他话音刚落,沙盘就开始震动,看来降坛的仙人被气的浑身乱战,狂风暴雨般写下四个大字:“小子无礼!”然后就消失无踪,再没有动静了。
但是周围的人都议论说,这人的嘀咕很有道理,倒是这位仙人表现的太没有风度了。
[衔冤]
曾有人无意中挖到一座古墓,年代久远,棺材尸骨都化成了灰,荡然无存。只有一颗心还完好无损,仍然是血红色的。
又有一块石碑,上面的字迹还勉强能够辨认。有人将之拓印出来,卖给当地的读书人,拓印本被一个官员得到,写的是——
白璧有瑕,黄泉蒙耻。
魂断水漘(临水的山崖),骨埋山趾。
我作誓词,祝(发愿)霾(同“埋”)圹(墓穴)底。
千百年后,有人发此。
尔不贞耶,消为泥滓。
尔傥(同“倘”)衔冤,心终不死。
最后写着一行:“壬申三月,耕石翁为第五女作。”
得到拓印本的官员想要更深入地了解一下,不料当地的村民担心被这件古怪事情拖累,就把石碑捣碎,和心一起沉进了水里,对外坚持说没有这回事。
仅从碑文来看,是有女子被冤而死,其父代为明志。既然古墓中发现的心完好无损,说明这女子确实是被冤枉的。但碑文中没有留下姓名年号,所以无从考证前因后果。致使这桩奇迹湮没无闻,实在是可惜啊。
(是可惜,千百年后,纵然昭雪,又有什么用呢?我倒宁愿她身前没有白担了虚名,至少爱过或享受过了。)
[自知]
康熙年间,有一个古董店商人,名叫李鹭汀,精于占卜。但珍重技艺,从不为人占卜,只是每天早上起来为自己占一卦,也不说占卜的结果。他说:“过多泄露未来情形,神明一定会憎恶的,所以我知之,我不言之。”
曾有人将他的占卜才华与著名易学专家康节(北宋哲学家,字尧天)相提并论,他说:“我哪儿能和康先生比啊,和他比,我只得了五六分的本事。”并举例说某天卦相显示会有仙人拄着竹仗来拜访他,在他的店里饮酒题诗。他大喜过望,早早地把店里打扫干净,焚了一炉好香,恭候之。结果到了中午,有人拿来一尊竹刻的吕洞宾像,想卖给他,雕的是吕靠着一个酒葫芦,旁边还刻着他那首著名的“朝游北海”诗(笑,是很有名,诗是这样的: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所以他说:“如果是康节先生的话,会闹这样的笑话吗?”
不知是不是因为精通占卜,将人情世态看得比较淡的缘故,他年过五十还没有娶妻生子,只纳了一个小妾作伴。某天有朋友来拜访,听到两口子在拌嘴,小妾一边哭一边数落:“这是什么事?!你怎么可以拿来和我开玩笑?”他着急地辩解说:“我没有开玩笑啊,是真的!”
朋友问他们在吵什么,他说:“大奇事!今天店里来了两个客人,卦相显示,其中一个是她前世的丈夫,而且和她还有一夜的缘分;另一个是她的下一任丈夫,缘分大概在半年以后。三任丈夫聚在一间店里,是不是千古奇事。所以我忍不住告诉她了,结果她就和我翻脸。然而这是命中注定,不能改变的,她和我翻脸也没用啊。我都没有生气,她反而生气,我都没有悲哀,她反而悲哀,我也不知怎么劝解才好啊。”说着露出一筹莫展的样子。
事后过了半年,李果然去世。他的小妾先被一个翰林买去,但是翰林的正室不容,所以一夜之后又被逐出,第二次嫁的很好,生活安乐。
这些和半年前李的占卜完全吻合。
(插话:总觉得精于占卜的人要么不能为自己占卜,要么就会不快乐,不过这位古董店主人倒是个异类,看来还是心性豁达与否在起作用啊。)
[梦中人]
作者纪昀的朋友庞雪崖刚结婚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身穿青衣,云髻高耸的女子,旁边一个人指着对他说:“这是你的新娘子。”
他醒来后觉得很不吉利,因为梦中所见的并非他枕畔的新娘。不料过了几年,他的新婚夫人果然去世,续娶了一个姓殷的女子。新婚之夜揭开盖头,居然就是当年曾经梦到过的那个人。
所以他有一首悼亡诗是这样写的——
漫说前因与后因,眼前业果谁定真。
与君琴瑟初调日,怪煞箜篌入梦人。(“箜篌入梦”的典故见于《太平广记》:一个名叫崔宇的读书人,和一个名叫薛肇的道士是朋友。薛曾带他到一座宫殿里玩,有四十几个女子在那里弹奏乐器。薛让崔挑一个陪酒,崔就挑了一个弹箜篌的女子。薛说可以将这个女子嫁给他,但得等几年。几年后,薛娶了一个姓柳的女子,就是他梦中弹箜篌的那个人。)
[写真]
有一个名为张无念的画家,住在京城樱桃斜街(在宣武区。插花:发现北京好些“斜街”的名字都很好听,最喜欢的是后海“烟袋斜街”,感觉烟斜雾横,带点颓唐,更多的是适意。而这个“樱桃斜街”也好听)。书斋的窗户用巨幅白纸糊成,没有窗格,追求采光效果。每到月圆之夜,就有一个女子的身影落在窗心,打开窗户却什么都没有。开始的时候张有点害怕,时间一长,并没有什么异样作祟,他也就习惯了。
某天晚上,他闲来无事,仔细看了那女子的身影,发现她的体态婀娜生动,宛然如画,就用笔在窗纸上勾勒出她的身影轮廓。从此之后,这女子的身影不再出现,但月圆之夜,又有美女从墙头望院子里张望。几次之后,张忽然明白,那是同一个女子,希望自己把她的模样画下来,流传后世。于是他就问那个女子是不是这样的,那女子不回答,也不消失,一任他注视许久,才慢慢隐去。
于是他根据自己的记忆,为窗纸上的身影补上容颜服饰,画成一张仕女图。画完的那天晚上,听到窗外有人轻声说:“我的名字是亭亭。”而后寂然无声。
这幅画名重一时,后来被某知府买了去。(看看,什么叫炒作高手!多么有效,而又多么优雅不俗。)
[解讼]
作者纪昀的父亲纪容舒老先生在江苏作官的时候,遇到过这么一件案子:少年强暴少女未遂。涉案的少年十六岁、少女十四岁。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少年游玩回城,看见少女在菜园子里摘扁豆,觉得她清秀可爱,一时忍不住就动手动脚。巡逻的人们听到了少女呼救的声音,就把少年逮住,送了官府。
案件还没有开始审理,两家的父母都赶来了,说这是一场误会,这少女其实就是少年的未婚妻,只是小两口没见过面,不认识,所以闹了这么一出。
按照当时律例,未婚夫妻间发生男女关系,属于“和奸”,没有“强奸”一说,而少年强暴未遂,也谈不上“奸”字,因此这案情变得很特殊,没法按律例发落。正在这时,少女也改了口供,说少年只是言语调戏,没有真的动手动脚。于是姚老先生就把那轻薄少年训斥了一番,当堂释放。
后来有人到他面前检举,说是少年的父母重金贿赂少女的父母,两家串通好了用假话把官司搪塞过去。而少女本人后来想想,觉得少年模样不错,家里又有钱,也就心甘情愿地跟着作伪证。
姚老先生说:“有可能是您说的这样,但是口说无凭。而且就算是这样,结果也无非是促成了一桩婚姻。又不是人命官司,没有沉冤未雪的受害者。让他们搪塞过去有什么关系呢。再说女孩子没有真的被玷污,她自己也答应了,双方父母也同意了,有媒有保,街坊邻居也没有质疑反对的,供词也都合情合理,真还不失为一桩好因缘。我宁可做那被‘欺之以方’的君子,干吗要从中作梗,非把一个十六岁的孩子送去充军呢?”(再次感叹,纪老先生真了不起啊。)
[负狐]
有一个姓柳的人,和一个狐妖是好朋友。柳家里很穷,狐妖常常接济他。他曾经欠人一大笔钱,准备把女儿抵给人家,又是狐妖朋友为他把欠条偷了出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狐妖常常来他家,他的妻子孩子都认识,常常问好聊天,但只有柳见过狐妖的样子。
后来这狐妖搞上了一个富家女,女子的父母很生气,想了各种法子驱逐它都不成功。最后悬赏一百两银子捉拿这狐妖。
柳氏夫妇听说了这件事,柳还没什么,他老婆却大动心特动心,怂恿他把狐妖干掉,好拿这笔赏金。柳还在犹豫,他老婆就使出了最厉害的一招,说:“这死狐狸能勾搭人家的女儿,就不能勾搭你的女儿?昨天他还给了你银子,特别叮嘱给咱家闺女做件冬衣,这是什么居心?你现在不动手,到时候可就来不及了。”
柳便被说动了(其实只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心安理得的理由),偷偷买了砒霜下在酒里,准备对狐妖动手。
然而狐妖早就知道了他的居心,一天晚上,柳和邻居乘凉的时候,狐妖忽然大声喊柳的名字,然后开始对众人讲述他们渊源流长的友谊,以及他为柳家做的种种贡献,最后揭发了柳要害死自己的阴谋。狐妖说:“我不是不能害你,只是和你相处了这么久,你虽然狠得下心,我却做不到像你一样。”说着把一匹布、一卷棉花从空中扔下,说:“你的小儿子昨天对我说晚上冷,要我送他一床被子。我虽然和你决裂,但也不能失信于孩子。”说着长叹一声,就要离去。(怎么感觉这么哀怨啊……)
这时,乘凉的众人都对柳冷嘲热讽,狐妖便又说:“是我自己不带眼识人,我也有错。但我哪里知道,人间世情果然如此险恶。现在我知道了,希望大家也从中汲取教训。”说罢离去,再没有出现。
从此之后,柳便为乡亲们所不齿,再没有人肯对他有所接济。只得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也不知下落。
[彩符]
作者纪昀的侍妾郭氏,是山西大同人,后来全家迁到天津。她出生的时候,母亲梦见自己买了一枝端午节的彩符,所以给她取了这个名字。
郭氏嫁给纪昀的时候只有十三岁,他们生过几个儿子,但都没有养大,只有一个女儿长大成人,嫁得很不错。
女儿的公公擅长推算命理,曾经为郭氏算过命,说她不能享长寿,应该死于四十以前(汗,还真是铁口直断,对亲家也敢说真话?)郭氏果然在三十七岁时去世。
纪昀被贬到新疆的时候,郭氏就已经得病,曾经在关帝庙求签,问还能不能和纪昀见上一面。签文是:“喜鹊檐前报好音,知君千里有归心。绣帷重结鸳鸯带,叶落霜调寒色侵。”她觉得签上说的是纪昀将在秋冬时节归来,两人还能再续前缘,觉得很高兴。但当时纪家有一个姓邱的门客听说了,说:“见是一定能见上一面的,但我担心最后一句不吉利。”
果然,作者是在六月的时候回京的,那时郭氏已经病得很重了。到了九月,忽然加剧,就此长眠。
郭氏死后,下人把她的故衣拿出来晾晒,作者看见后很感慨,赋诗两首——
其一:风花还点旧罗衣,惆怅酴醾(就是“荼蘼”的另一种写法)片片飞。恰记香山居士语,“春随樊素(白居易的爱妾)一时归”(见白居易《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
其二:百折湘裙飐画栏,临风还忆步姗姗。明知神谶曾先定,终惜“芙蓉不耐寒”。(寒山曾有诗句“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作者原注。)